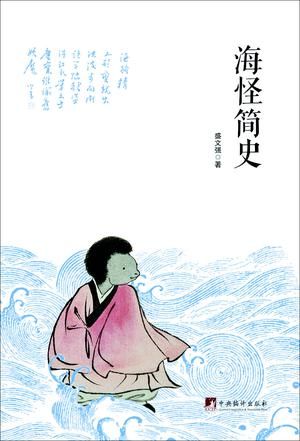
《海怪简史》 盛文强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意大利小说家迪诺·布扎蒂有“意大利的卡夫卡”之誉,他写过一篇叫《海怪K》的短篇小说——K正是卡夫卡的首字母,也是其《城堡》《诉讼》等多篇小说的主人公;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作品是现代文学的开端,而K故而也是最初与最著名的现代文学人物。而在布扎蒂的笔下,那被称之为K的海怪,是个黑色的庞然大物,传说中,它固执地尾随人一生,为的就是要吃掉他。但在小说所展现的事实层面上,那个自幼在海上被海怪K盯上的孩子带着毕生的恐惧,始终远离大海,过着平凡的日子,直至衰颓到死亡将临的时候,独自去海上面对他终生的“追随者”,却亦真亦幻地听到K告诉他:多年以前,海神命它捎给他一颗宝珠,少年凭此可以成为帝王、伟人或者富翁,结果现在,宝珠、海怪以及那个逃避了一生的人的生命,统统失去了意义……
比之古典的利维坦或者现代《老人与海》中的大鱼,这个叫K的海怪更具有寓言色彩以及更怪诞,给人留以浩大如海的阐发空间。被海怪尾随终生的,或许并不止是短篇小说中的那一个人物,可以说,现代人普遍都经受着如许命运,处在各种各样对未知的焦虑与恐惧中规避着命运的意外恩赐,庸庸而碌碌。这个来自未知世界的庞然大物,某种不明意志、或莫测命运的使者,因此可以看作是错综复杂而具有压迫感的现代性的一个喻体。这个海怪K,是我看到盛文强所撰《海怪简史》一书的书名时,马上就从欧洲来到我的脑海中的形象。虽然,《海怪简史》所涉是“半岛”即山东附近以及其东、北、南远近的海域,总体上说,不出东方的传统与视域,但《简史》的表述却是十足的现代经验,这是一种略省扼要的对过往的清理,至少在名义上宣称以简驭繁,唯在信息与书籍都繁荣而密集的环境中,招引现代读者迅速投入文本又很快撤离,带走袅袅绕梁的余音——这正是简史作者对读者抱有你“来了”,你“见了”,你“赢了”(也可以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式的自信。而对海怪的兴致,也是博物书写重返文学的现代趣味,对妖怪——包括占地球表面积比陆地更多一倍的海里的更多妖怪——的描述与记录,富有超出字面意义的喻指色彩,而在博尔赫斯诸如《想象的动物》之类的文本出现后,从神话与民间传说中走出来,从哥特、奇幻的亚文化与类型小说中脱颖而出,日渐成为一种不可轻视的文学题材。
现代性,在《海怪简史》这里,还表现为一种立场与视角:叙事者作为一个脱离了故土、偶尔在回忆及短暂的行程中稍稍重返海滨的渔乡游子,试图用词句来显现其无法返回的过往,以及渔村乃至海洋的往昔。作者有意高频安排了这样一句话作为套语出现在书中各篇里:“你知道,这是许多年以前的事情了。”直接面对当代读者,却将诉说的焦点从当下移开;一个个故事于是在遥远的时间坐标点上,滋生人是物非、沧海桑田(这几个字的出处,即神仙麻姑的口述史,本身也可以是《海怪简史》中的一则)的氛围。对海洋及其中妖怪的陈述,即此成为一种有景深感的家园缅想。其怀思的对象,那个叙事者与作者共同的故土,海陆相接、相互延伸的所在,具有两倍逝反的特征:一则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离开,再者是故土被裹胁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在古早时候——叙事者的童年、甚至可以扩大到渔村的童年以及人类的童年时代所产生的那些富有魅力的传说,在成长过程亦即重合的现代化进程中,被理性与更广袤世界的经验所边缘化、祛除与抛弃。
这本讲述海怪的故事集,由是采用回溯与倒叙经验的方式,将自己伪饰为一部线条明快的史书。该种策略当然是汉语说部的惯伎,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讲之史,却是自古以来所罕见的:是关乎神秘海洋中神秘海怪的故实与野谈。在汉语经验中,海洋素来位于纪实不能坚硬处,为乏力、泡沫与汪洋所包裹,留有大片空白与无数奥妙,海岸线成为现实与想象的分界。自《山海经》以降,甚至,就从《山海经》开始,山海一直都是偏义复指的语法。虽然我们在气候上还饱受海洋性的影响,在居止与经历方面,海洋却一直是道听途说的幽微事实,往往不曾涉足,甚至鲜有远眺:黄河入海流、海客谈瀛洲,从《庄子》到唐人,海洋只是抒情与传奇的视角。海洋与海怪的事实需要从文献传统中细心钩稽出来,才能显现其恢闳阔大的体量。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要隶属于集部的小说,却也担当得起史部的职责,为自古而来关于海洋的奇瑰念想,收纳在一个又一个海怪的形象中,构成一个幻想向度的博物学样本。
想象力的发散与收纳,可使文本进入文学或者历史的脉络;但还有第三条道路,在传统中对应那些说理的著作:子部。稍稍引申,子部书主要是其中那些指名文本即诸子著作,又尤其如《庄子》,则在文学与诗性之外,还有一层想象力的返回与沉淀。由物及人,返诸己身。博物学在这样的阶段,就拥有了叩问智慧的倾向,而不再迷失在物的密林中,博而不约了。在《海怪简史》中,我注意到,作者对海怪们的表述,亦多有超出史籍与旧书之处,例如《长股人》一篇结以“须知:我们都是长股人和长臂人的后代”一句,十分隽永,耐人寻味,含义渊远。这是《海怪简史》向《庄子》的几层呼应之意,此外,就全书的题辞引用《秋水》一篇中“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一段,也可以作为例证。再者,一如《庄子》及其他子书有分出内外篇,《海怪简史》亦有外篇与内篇的设置。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设置或许还是双层的,在目次上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显明的一种,如果细读自《海和尚》起的诸篇海怪,我们可以发现,叙事者往往会在某一个海怪的故事中,也分出内外,或者依人类学称之为主位、客位两种叙事视野,从生活与典籍的不同角度,从主体介入与道听途说的双重立场,把一个海怪讲上两次,又合并为一个完整的篇章。依我之见,这达成了叙事者与海怪之间分离、迂回而又相互注视的过程,完成了人与物、经验与想象的关联,而文本于焉意义圆满。(朱琺)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