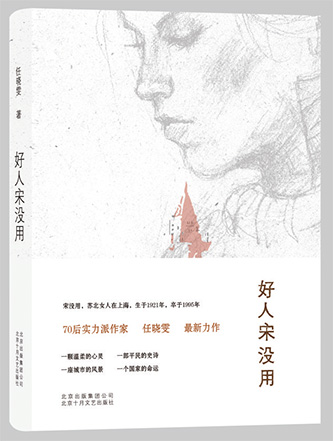
宋没用既是一个人,又是一群人。她是特定年代特定身份下妇女形象的缩影。与其说女主人公宋没用是母亲腹中胎儿,不如说是作者笔下的产物。而作者不仅给主人公起了“没用”这般戏谑的名字,还在一开始就给女主人公发了张好人卡。所以这本书从标题开始就勾起了读者的好奇:答案已出,线索自寻。
不言语,在这隐忍的一生
宋没用生于1921年,卒于1995年。生于苏北农村,长于上海药水弄。刚出生时因为是幺女,被母亲嫌弃,起名叫“没用”。用时兴的词语形容,宋没用是城市务工子女,是外来流动人口。药水弄就是她的家。药水弄等同于上世纪上海市郊的棚户区,周围是臭水沟,穷人住的是旱船、棚屋、滚地龙,卫生条件极差,一到梅雨季节就瘟疫肆虐,穷人没钱就医,仰着头等死,死的人多了,活着的人买不起棺材,就把尸体草草打发了事。这里的男女老少大都从外地迁徙过来,没知识少文化,只祈求一口饭吃。多的是拾荒儿童和街头混混,稍微好一点的,去寻个搬运工或者人力车夫的活计。宋没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宋没用在母亲去世之前似乎很少说话。她是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因为她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也因为她的言语不能被听到:乱世光景里,她只能被当成是谋生的工具。她一直缄口不言,只有听话的份儿:两个姐姐的话要听,哥哥的话要听,爸妈的话更要听。她在挤挤攘攘的棚屋里缩着脑袋,在脏兮兮的药水弄摸爬滚打,在陌生的上海滩捡拾垃圾,睁大双眼竖起耳朵,默默注视着身边奇奇怪怪五花八门的事。她从不反抗,父母让她做什么就做什么,实在委屈就跪在黑夜里痛哭一场。她在小小的年纪目睹了大姐患瘟疫而死、二姐在一次火灾后不辞而别、大哥做了汉奸、父亲酒瘾发作胡话连天、母亲老死在漏雨的棚屋下。正是想要扮俏做女人的年纪,宋没用回想起母亲的抠门儿、暴躁和无端打骂,想起在本该玩乐的年纪饱受的劳苦艰辛,一向隐忍沉默的她,终于生平第一次张开喉咙,冲着死去的母亲说出压抑已久的那句“我恨你”。这一声“我恨你”既是隐忍委屈的宣泄,也是对世界愤懑的宣告,更是对命运无奈的感慨——生不逢时、命运不济的她,除了向死人发出一声哭诉,还能做什么呢?
不言弃,在这“没用”的一生
宋没用的名字经历了两次变化。出生时因为是幺女被母亲嫌弃,起名叫“没用”。在老虎灶的日子里,她不是宋没用,是宋梅用。后来梅用的三儿子平生给母亲办身份证,又恢复回“没用”。
宋没用的生活也经历了两次变化。生活在药水弄时,她上有哥哥姐姐父亲母亲,是家里最没用的一个。后来去了老虎灶,帮老板娘杨赵氏干杂活打理店面,和杨仁道过上了苦中作乐的日子,还给杨仁道接连生了几个孩子,这时她的生活像寒冬里的腊梅,终于吐露了些许芳香。再后来杨仁道被抓走杳无音讯,宋梅用一人带着五个孩子寻求生路,并在孩子一个个长大后逐渐衰老,孤苦无依的她又成了没用的废物。这让人不禁想起《悲惨世界》里冉阿让的结局。冉阿让在牢狱里做了19年苦役后被米里哀主教感化,做了不少善事,临死前养女却没能赶上见他最后一面。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认为,人的一生要经历从自我到本我再到超我的过程。没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对整个家庭来说是个累赘,她自己也不明白存在的意义;后来她去了老虎灶,改叫“梅用”,她的人生开始有了一些不一样的色彩:有了疼爱自己的男人,有了自己的亲骨肉,有了养家糊口的能力和心头的几多牵挂。这时的她对周围人是有用的,自己也是舒心的;再后来杨仁道被抓,她一个人拉扯大五个孩子,之后慢慢衰老。她观念守旧,顺应不了这变化巨大的时代,劝不动成年的子女,甚至连自己住哪儿都决定不了。她的生活重心早已不在自己身上,她的作用也慢慢减少了。
死生循环,新老交替,从娘胎来,到泥土中去。在动荡不堪的浪潮里,更多的人是时代的牺牲品,在浪尖上挣扎,在海面上浮沉,在逆流中奋力向上游。《好人宋没用》是小人物的大事记,是大时代的缩影,是一个普通妇女的普普通通的一生。或许,每个人的一生都像一条小船行使在漫无边际的海上,躲得过礁石躲不过风暴,总要在一次次浪涛中寻找平衡。
不生畏,在这流浪的一生
没用的住所发生了三次变化。从小跟着全家人在药水弄长大,直至爸妈去世,她一个人到老虎灶求生,这是第一次变化;杨仁道被抓后,她带着几个孩子投奔佘太太,过上相对稳定的生活,这是第二次;最后一次搬家时在战生做生意赚到钱之后,行将入土的她听凭儿子的安排搬进了装潢体面的公寓,直至最后孤独死去,这是最后一次。
地理位置的迁移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命题。通过地理位置的变化可以折射出主人公心理心态、生活状况甚至社会环境的诸多变化。住所的变化首先意味着没用身份的变化。刚开始时,没用是个废物:母亲嫌弃她是个负担,给她起名“没用”;在老虎灶安营扎寨,没用成了店铺的帮手和杨仁道事实上的妻子,逐渐又成了老板娘和孩子的母亲;被赶出老虎灶后携家带口在大户人家的洋房里安身立命,她成了富人家的佣人和一个靠双手支撑起家庭的寡妇,生活过得紧凑也还停当;再后来孩子一个个长大,她被安排到新式公寓里,成了碍手碍眼的老太婆,跟不上社会变化的落伍老人,被儿女逐渐遗忘的老母亲。
而随着没用住处的迁移,上海的政治风貌也跟着在变。没用住在药水弄时,这时期的上海恰值殖民地统治时期,深受外来思想的碰撞——上海的街市上已经开始兜售印着大胡子洋人的香烟,洋镜洋伞,西装礼帽,洋人出没的地方还会有洋行戏院旅馆舞厅等舶来品。而构成这城市图景的另一面,则是纷纷来上海谋生的外来穷苦无业民工。外来人口聚集而无处安置,挤在又脏又臭的药水弄……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上海市郊特有的生活面貌。
焦点转移到老虎灶,日军入侵,上海不断遭受日军炮火轰炸,蒋介石统治下,货币贬值严重,外币充斥,生意人审时度势囤积货物,普通人家的生活风雨飘摇。接下来画风突变,小洋房里住着的资产阶级代表随着共产党的到来沦为斗争的焦点。佘太太的丈夫被抓,曾经的佘太太变成如今的倪路德同志,从资产阶级小姐成为普通劳动群众。这时,没用的生活才慢慢有了好转。
生活不允许宋没用待在同一个地方,社会变迁也不允许。她一再搬家,生活一再变化,社会也同样在变。可是没用这一生究竟看清楚这外在的更迭没有?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大字不识的她像一株风中飘荡的芦苇,却不知道这风来自哪儿,又要飘向哪儿。她试图掌握自己的命运,却只是勉强不被命运扼杀。没用一生不反抗,只偷过一块金条,还是为了给哥哥谋条生路。她是乱世里的好人,又是乱世里的幸运儿。
不回头,在这未知的一生
没用的一生是飘摇的、多变的、隐忍的,她跟随父母从苏北农村一路踉跄走来,在时局动荡的大上海落地生根。她是沙漠中的白杨,石缝里的竹子,沼泽中屹立不倒的芦苇。如同当初陪着父亲宋榔头就医时死死攥紧的钱袋,她攥紧行头,为了生存随时离开旧宅,驶入下一个航程。
文学的价值便在于它可以照进现实,指导我们的生活。文学存在的原因在于它的普适性。在宋没用生活的时代尚且与过去频频告别,反观现在就更是如此。李叔同在《送别》一词中写道,“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往昔如此,今日便更处处是别离,而且是千军万马,浩浩荡荡:高铁动车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登机口处洋洋洒洒的鲜花眼泪,异国他乡的越洋电话……这是一个集体告别的时代,有的人一去一年半载,有的人再也不曾回来。可慢慢的,异乡追梦的兴奋劲儿逐渐散去,生活的负荷和现实的残酷使人喘息不得、疲惫不堪,于是又开始留恋往昔,所以这也是一个集体怀揣乡愁的时代。
宋没用的生活和她的名字形成了鲜明对比,生活的重担不允许她花费太多时间去凭空吊念,她只有拼命向前奔跑才能不被生活击败。好人宋没用在苦难面前向死而生的态度,一败涂地也能从零开始的勇气鼓励着我们每个人: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
(《好人宋没用》,任晓雯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