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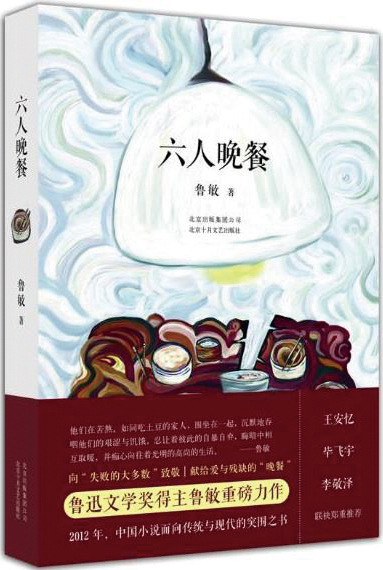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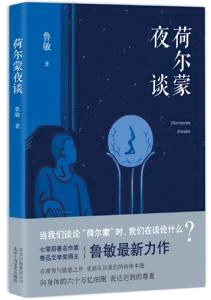
我所理解的文学,是以苍耳为主要聚集点,苍耳就是我们人类,它柔软,有刺,有汁,有疼痛与枯荣。最为理想的作品,是从这些小小苍耳的身上,感知到特定空间或时代的流变,流变中的冷酷与滚烫、对个体的推送、佑怜或伤害,感知到那既属于时代、又属于人的爱与哀。
我对毛茸茸的幽微地带有兴趣,这些越轨者,就特别富有重叠、交叉、易变的心理区域,他们是大时代下有自选动作的小苍耳,集中笔力于他们,有可能会以特别的方式获得与巨躯的共振——这种“在别处”的心态,我认为就是人与时代的“共振”之一种。
行 超:我记得《六人晚餐》刚出版的时候,评论界有人认为,这部作品在个人命运、内心起伏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等方面刻画得很出色,但是没能充分写好转型时代这样的历史大背景。“如何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这个问题多年来似乎一直困扰着“70后”、“80后”作家们,时隔多年,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部旧作?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新的认识?
鲁 敏: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打个比较老土的比方,我觉得人就是挂在时代巨躯上的一只只苍耳。时代行走跳跃,苍耳们也就随之摇晃、前行,也不排除在加速或转弯时,有少许被震落到小道上……我所理解的文学,是以苍耳为主要聚集点,苍耳就是我们人类,它柔软,有刺,有汁,有疼痛与枯荣。最为理想的作品,是从这些小小苍耳的身上,感知到特定空间或时代的流变,流变中的冷酷与滚烫、对个体的推送、佑怜或伤害,感知到那既属于时代、又属于人的爱与哀。
但由此也常形成一种目的化的理念,认为时代巨躯的起伏轮廓、激荡风云乃是文学的大抱负所在,区区苍耳不过是切入点与承载物,它们的悲欢离合再精彩总归也是小了的、失之精微毫末,对张爱玲、汪曾祺就常见这方面的婉转批评。我倒是觉得,苍耳从来都不是挂在虚空中或无缘无故、孤零零的一枚,哪怕它从巨躯身上掉落下来了,依然有它掉落的姿势与价值。所以问题的根本可能还是,我们能把苍耳写到什么程度。
就像大家常常会说到,“70后”这一代的写作,总写小人物,太过生活流、琐碎化,缺乏大格局,缺乏历史意识与厚重的精神维度,这确实需要进行讨论和反思,比如,苍耳本身的典型性与提炼度不够,呈现为过分随意的个性化写作等。但若换一个角度考察,这一代人的文本气质与他们所书写的苍耳们,那些琐碎微渺精致、与宏大理想英雄主义的决裂,所折射出的不正是其所处的外部社会与时代的某些特征吗?
从这一角度来看,《六人晚餐》正代表了那一阶段我对个人与时代关系的一种理解。这六个人的相互关系、伦理取舍、起伏路线,是受制并折射出时代风潮的,但我并不会去特别的强调这一点。做资料时,我搜集了所涉产业重组、国企改革、关停并转、下岗分流等许多资料,但我不会打呼哨一样地在文本里让它们有意出声,最多会暗中撒一两把小豆子。我更想竭尽全力去创造的,是“晚餐”桌上那六只苍耳在其时其境的、来自末梢的颤动。
但在现今,我又觉得,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真的有主次、有依附吗?有这样泾渭分明的孰轻孰重?天地人当是合一的吧,并不需要把时代与个体提淬出来分别计算比例与权重。比如我们看《苔丝》《白鲸》《老人与海》《安娜·卡列尼娜》,包括《鼠疫》,就算加缪特意虚构了一个黑色时疫的社会背景,但其真正的着力点,还是某种困境中人性的软弱或力量。而与此同时,你在所有这些人物身上,又能看出性别、阶层、伦理、宗教等在人类文明洗礼下的不同进程。苔丝、老人、亚哈船长,如到了另一时代或国度,就会是另外一个故事。
厚颜说句有点托大的话,我写《奔月》,也是在这个方向上做出的一次小小的实践,让小六去置于特定情境(自我出奔),从中呈现人性中委泥与飘逸的永恒矛盾,但这必定是属于当代中国都市女性的“这一个”,小六的行动与逻辑不会是嫦娥、娜拉、爱玛的。
从《六人晚餐》到《奔月》,也差不多算是不同阶段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行 超:你好像一直对于“越轨”有很大的兴趣,从《荷尔蒙夜谈》到《奔月》,你的写作风格与之前相比有了一个明显的转折,似乎更“大胆”、更“果敢”,一种天性中向往的生命自由、生活自由与写作自由被释放了出来。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鲁 敏:是啊,还有同行跟我开玩笑说这是中年变法,谈不上的。我对写作既有职业化心态,也有偏执的倚重,重到此命所系的地步,这心态并不很好,但也可能正因为是这样的心态,写作会相当直接地反射出我对生活、生命和“我之为我”的胡思乱想。
譬如在现阶段,好像对生活本身有种崇拜与热爱,因热爱而愈加不可忍受它的平庸、麻木与一应之定规。因此,我会有意注目,并以欣赏、挖掘和怂恿的眼光去注目“越轨者”,我希望通过他们来表达和丰富我对生活的热爱,表达这激越而伤感的中年之爱。从写作层面看,这也会使我选择放弃平缓、老熟、节制、雅正等审美方向的权重——当然,写作时并无这样的谋划,谋划不了的,只是在回看时,才会发现一些煞有其事的轨迹。
行 超:在小说《奔月》中,小六以身试法地证明了在现代社会中,个体的人是“无处可逃”的。很多年前你曾经写过一个中篇《细细红线》,与《奔月》处理的是类似的问题,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在别处”生活的幻想与向往。写作对你来说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逸吗?
鲁 敏:写作有平衡和对冲世俗的功用,所以常有人用它来做钟形罩与隔离区。对我来说,倒不是这样,这是我的职业与志向所在,假如真有逃逸之心,反而会远远地离开写作吧。
那我为什么又会开足马力地写类似那样的逃逸者、越轨者呢?其实我想通过他们来表达我对生活和世界的感受,这个感受有些是发自我内心,但更多会考察他人与外部世界,在内部与外部之间寻找共通性。我对毛茸茸的幽微地带有兴趣,这些越轨者就特别富有重叠、交叉、易变的心理区域,他们是大时代下有自选动作的小苍耳,集中笔力于他们,有可能会以特别的方式获得与巨躯的共振——这种“在别处”的心态,我认为就是人与时代的“共振”之一种。
行 超:小六的失踪反而给了身边的人一个重新认识她的机会,不管是贺西南还是张灯,在寻找小六的过程中,都完成了对这个“熟悉的陌生人”的重新认识。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身份、职业、社会地位、人际关系等往往会遮蔽这个人的本性。小说最后连续几个“小六快跑”,“她总算是实现她的妄想了啊,随便哪里的人间,她都已然不在其中。她从固有的躯壳与名分中真正逸走了。她一无所知,她万有可能,就像聚香刚生出来的那个婴儿”。对于小六来说,与其说这是一次回归,不如说是一次重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失踪”,或者说“出逃”是不是一种对现实的消极抵抗?
鲁 敏:“出逃”“失踪”,是消极抵抗吗?我恰恰认为小六是到目前为止,我笔下最为勇敢、最具自我意识和行动力的一个女性形象,她敢于打破哪怕并非一无所错的现状,去实践那个曾经涌上所有人心头的大胆妄想,她冲破了本分、责任、亲情、血缘、伦理、道义等几乎所有的定规与约束,奔往那无可参照、万劫不复的地带。
所以我并不担心人们会从书名联想到嫦娥,因为小六完全是现代和当下的异质的嫦娥,她同样想摆脱世俗与人性的重力,追求本我的发现与飞升。这或也是社会发展到现代性文明阶段的一个特征,是人类在走过了生理、安全、社交、情感等需求之后的更进一步:对自我的确认与探索。
行 超:费尽心思策划了一场“失踪”的小六最终还是选择回到自己原来的生活,但是这时的现实已经完全改变了,她的丈夫、情人、母亲以及周遭原本熟悉的一切,仿佛都换了个样子。小六最后还是回来了,乌鹊也不过是另一个南京。那么我们是否还要追问这场“失踪”的意义?
鲁 敏:《奔月》出来后,关于小六“出逃”的意义所在,是被探讨、也是被追问得最多的问题。从这些问题其实也能看出我们对长篇文体的考察与度量标准。比如说:对“中心思想”的期待。大家一起跟着主人公小六辛辛苦苦地出走、折腾了一大通,然后又回去,又没回得去……请问你到底想讲什么?要证明什么或得出什么结论吗?如果我说,没有啊,我并没有确定和高明的结论。啥?没有?这显得好像很不合理。
好吧,于是我接着说,我想表达的就是这种不可概括和终结的人生迷境,因为人生不是数学题,并没有最终答案——就算有,是读者自我达成的,是我提供的这部分,与你的个体经验碰撞后的结果。这会让一部分人觉得明白了。
但还有一部分,仍会显出不够满足的目光。于是我只好进一步阐释(我很不喜欢这样说得太多):我写的是人们终身的角色困境;写的是生命与生命相遇的虚无与偶然;写的是作为人,即使在异度时空之下也永远无法挣脱的本来面目;写的是我们这短促一生里,对另一条“林中小径”的不可确证与不可触碰……
人们对这样的回答满意吗?也不尽然。所以你看,这里还包含着另一个阅读上的偏见与傲慢:结局期待,并且是偏暖调性的期待。他们总是希望看到人物的攀升(而不能忍受对原点的回归),感悟与收获(而非无悟之感、不获之获),希望看到从无到有(而不能接受从有到无)。
所以,与其说追问《奔月》里小六出奔的意义,不如先追问一下我们对长篇的审美维度,我们对终极意义的痴心妄想,我们对存在与虚无的定规之见——譬如,我恰恰就是以虚无的终场,来表达疼痛存在的自我。
行 超:你曾在多个场合提到自己对于虚妄、荒谬等等不可言明的偏爱,比如“我偏爱不存在的荒谬胜过存在的荒谬”;“以小说之虚妄来抵抗生活之虚妄”……可是从你的小说写作手法上看,你应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作家。你怎么看待这“虚”与“实”之间的矛盾和关联?
鲁 敏:粗暴地概括下,这虚与实,可以说是灵与肉的关系。小说内部的灵的部分,我常常有点形而上的探索性,因此有虚无的灰调感。但肉,即及物的写作内容与技术手法上,如你所说,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写作。
最近我重翻了下萨特的《恶心》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笔记》,你看它们,灵是形而上的,肉(即文本主体)亦相当枯简,是寓指化的。这样的写作,对作家和读者都有着太高太高的要求,我还做不到。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像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则是用传统叙事手法来写现代性内核的。他们教会我很多东西。最主要是,现实主义手法对现阶段的我来说,的确更得心应手,这也是从“我能”的角度来考虑的。
那么矛盾有没有呢?有。比如有一些读者,有时会对这两个看起来像是两个风格的灵和肉感到迷感。以《奔月》为例,读者就会用现实逻辑来与我探讨:一个人用别人的身份证,能在外头蒙混两年?或者,那个警察太不负责了,怎么能劝她不要回去呢……情节的隐寓或人物走向的设计,对写作者和读者都是考验,也是阅读契约中最为微妙的部分。
因此,为了中和这两个方向,也为了不断地提醒读者:我写的不是完全的“现实主义”,我在《奔月》里特意置放了许多极为戏谑与荒诞的细节。比如“给亡灵烧纸钱”、“家族遗传症”、“失踪者家属联盟”等等,以此来间离和柔化虚实之间的冲突。
行 超:写《奔月》的故事似乎是你多年来的一个心愿,小六的心病多年来也时时困扰着你。写完这个小说,这种困扰减轻一点了吗?
鲁 敏:《奔月》确实是我惦记良久、终于得偿的一次写作,但咱们前面也说过,不论什么主题,包括《奔月》,一定是我的内心思虑与外部之间的化学反应,一次写作,就是对一个主题的开拓、挖掘与偿愿。小说《奔月》了,我反而落地了。新的主题,又将在混沌中慢慢地缠绕上来。我耐心地等待着。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