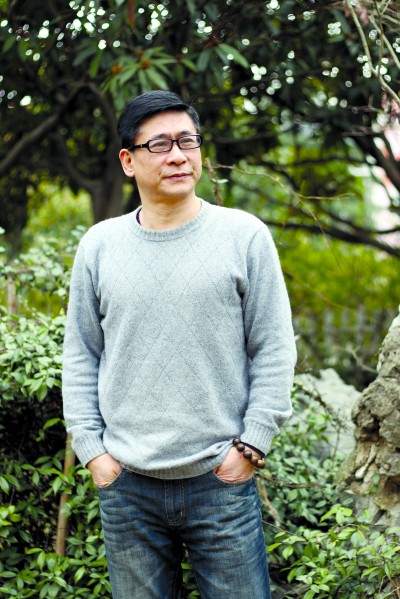
作家朱辉
作家朱辉凭借短篇小说《七层宝塔》于近日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朱辉说,相对于长篇小说,他更喜欢写短篇,因为长篇可以是大刀阔斧,而短篇则更适应镊子、钳子和手术刀。对理工科出身的他而言,科学思维让他明白很多事不可以想当然,而文学创作又能让他获得更多自由的想象,“可以写自己从未干过的事。”他相信,如果不当作家,他一定能成为一个好侦探。
朱辉,《雨花》主编,一级作家、教授,为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有长篇小说《我的表情》《牛角梳》《白驹》《天知道》,中短篇小说集《红口白牙》《我离你一箭之遥》《要你好看》《和辛夷在一起的星期三》《视线有多长》《夜晚的盛装舞步》等多部。有多篇作品入选各类年选和其他文学选本,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扬子江评论》年度文学排行榜等多种排行榜。曾多次获得紫金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和短篇小说奖、作家金短篇奖、汪曾祺文学奖等奖项。
□本期嘉宾 朱辉
青年报特约访谈人 何平
1 我如果不当作家,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好侦探。小说家的天赋权利,就是可以写自己从未干过的事。
何平:我注意到最近这些年评论家谈论你基本上把你作为一个专事短篇小说的作家在谈,《七层宝塔》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之后可能这样的印象会进一步强化,但大家似乎忘记了你曾经是一个很不错的长篇小说作家,你应该正式出版过四部长篇小说——《白驹》《牛角梳》《我的表情》和《天知道》。在很久不写长篇小说之后,回过头来,你自己怎么看这些长篇小说?
朱辉:我喜欢写短篇,并不代表我只写短篇,或者只能写短篇。我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在写了许多中短篇之后,大概2000年到2007年,我一口气写了四个长篇,就是你提到的这些。《我的表情》是第一个,我记得是在日本开始起笔的,写的是初恋和初恋的复辟。关于初恋,我的感觉是一个人只能写一部,多了就掺水了,我写得很诚挚,贺仲明兄曾说,《我的表情》是“文学含量很高”的作品,《长篇小说选刊》选载过。《白驹》是第二部,关于抗战和家族史,让我的祖辈在小说中复活,这是我的夙愿。我认为《白驹》算是我的代表作之一,原因是,它达到了这类题材我的最高水平。《白驹》获得了紫金山文学奖长篇奖,作为一个当时的业余作家,这并不容易。《牛角梳》写的是阴谋与爱情,女人的希冀、欲望和手段,在纯真爱情的衬托下,应该很突出,很扎眼。有人因此谑称我为“女版张爱玲”,说女主是“男版于连”,我不觉得完全不能接受。《牛角梳》我写得很恣意,很畅快,我第一次完全抛开了自我束缚,第一次把我对语言韵律的理解呈现出来,我确认了小说仅不是用来看的,更是用来读的,作家应该为有心的读者提供朗读时唇齿间的快感。《天知道》最长,30万字,是一部戴着侦探小说面具的社会小说。传统的侦探小说把杀人变成了艺术,但是,杀手的驱动力,要么是钱(遗产、保险之类),要么是情,要么是嫉恨、虐杀之类的变态心理。《天知道》不一样,杀手的心理动因具有社会性,乃至正义感。他的杀人甚至具有某种神圣性。《天知道》写了两年,让我体会到长篇可怕的消耗,消耗资源,消耗智力,消耗体力。因为我是业余的,还有饭碗要养护,2008年后的十年,我就只写短篇了。
四部长篇,写法和主题都不同。有一种善意的提醒:你缺乏把自己塑造起来的坚定。好吧,我接受。乡土、家族史和广阔绵延的时空更能引人关注,我岂能不知?但那时不是年少轻狂吗,凭着兴趣,依着感觉,按照自己的艺术标准,四个长篇也就这么写出来了。(笑)
何平:从你自己的写作经验看,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对一个作家的写作状态有什么不同的要求?就你自己的写作而言,你不写长篇小说也已经好久了,甚至中篇小说也很少,这样的结果是短篇小说给你带来别样的快乐,还是外在的局限使得你不得不作出这样的选择?
朱辉:写长篇,应该具备四个条件:阅历、技能、时间和体力。写短篇,大概只需要两项:技能和时间。短篇对技能的要求更高,对时间的要求倒不那么苛刻。其实,虽说业余,我的时间写中篇还是可以的。但短篇对我诱惑更大。我上班时不能写作,但可以发呆,发呆就是在谋划,也许突然灵光一现,我马上就可以写了。在有限的篇幅里完成一个艺术品,这是多么快活的事情。
何平:还说长篇小说,你的四部长篇小说题材迥异,结构也完全不同,尤其是《天知道》将类型文学的悬疑引入所谓的严肃文学创作,这条道路如果认真探索下去其实很有价值,哪怕我们就以《天知道》为样本,这样的实践也是有意义的。
朱辉:是的。我的中短篇不少也涉及探案。这是我从小就有的兴趣点,其实也是人类这种好奇的动物的一个天然兴趣点。
热爱故事,着迷于悬念,这是人类的一种习性。从这一点来说,侦探小说永远有它的读者。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案例从古至今都是人们口耳相传、津津乐道的话题。即使“谁是凶手”已经揭谜,案件的过程也大可探究,发案的起因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许多案子悬念迭起,处处都是谜题。从阅读心理讲,某个人被杀了,被抢了,被骗了,而我没有,还可以在这里听故事,他难免获得一种庆幸安宁的感觉。作案者因为情或钱,实施了凶案,而我持身守正,没干坏事,这无形中加持了自己的道德形象,更不用说置身于事外探幽烛微的智力乐趣了。中国文人显然深知其中三昧,作为一个缺少小说理论的国家,自唐宋传奇开始,到明代话本小说再到清代公案小说,探案小说不绝如缕,显然有其内在逻辑。
在上大学之前,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曾读过几乎所有被译进的外国侦探小说,爱伦·坡、柯南· 道尔和他的《福尔摩斯》、埃勒里· 奎因的《希腊棺材之谜》和《法国粉末之谜》让我和弟弟近乎于疯狂,两人只能约好轮流读,并且不可透露剧情;英国的威廉·柯林斯大概知道的人比较少,不知道怎么的,他的《月亮宝石》出现在我家中,似乎是从知青那里传来的,我看得心惊肉跳又欲罢不能,至今我还记得书里一幅阴森的插图,在书在双数页码,一个“双肩崎岖”(其实就是天生肩不平)的女佣举着烛台站在黑暗里,我就此学会了用“崎岖”来形容人体;阿加莎· 克里斯蒂的作品是在大学期间的图书馆读到的,主人公波洛的大烟斗和帽子,至今仍以影像方式保存在我家的抽屉里。
何平:所以你的创作正是得益于这些阅读经历。
朱辉:是的,我说这些无非是说,有时读什么书,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至今认为,我如果不当作家,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好侦探。小说家的天赋权利,就是可以写自己从未干过的事。
写“密室小说”,或者“本格推理”,我以为前人已几乎做到极致。他们表现的是“杀人艺术”,是杀人者与探案者的斗智斗法,是智力游戏,说到底,是写作者的左手和右手的较量。这是侦探小说家的兴趣所在,也穷尽了他们的智慧。于是,另一个对文学而言更为重要的使命被他们忽略或者悬置了。好吧,也不算悬置,是他们过早的落实了,他们前置性地落实了罪犯作案的动机,几乎不进行任何掘进和开拓。无非是:情欲,被欺骗或背叛;钱,股票、保险和遗产;家族世仇。基本就是这些了。更多样化的动机和动机深层的东西,被简单化了。除非展示这个案件的发生和侦破绕不开作案动机,侦探小说家完全没有兴趣花费任何智力。
这是一个遗憾,或许这也是正统文学界基本不把侦探小说纳入研究视线的原因——在这里插一句,这大概也是金庸之类武侠小说被摒弃的原因之一。是的,人性的丰富多姿和黑暗幽微,是文学的主要标的。但是,对动机的简单化,却也是传统侦探小说难以避免的不得不然,是无可奈何:他需要把罪犯藏到最后,哪怕他第一页就已出现。他必须藏,罪犯和作家齐心协力,一起在玩隐藏游戏。如此,透露动机的任何线索,都只能成为草蛇灰线和蛛丝马迹。他不能进行任何心理描绘,更遑论心理分析。
2 小事情吹吹牛可以,但在写作上,断不可自吹,把自己吹成皮筏子,以为就是普度众生的渡船。
何平:这也是你写《天知道》的原因?
朱辉:这是一种难以逃遁的模式。这是一个引力巨大却又看不见的黑洞,你只要写侦探小说,你就难以摆脱这个模式。但是,为什么不能试一试?真的就没有其他可能了吗?某些犯罪心理,难道不更幽暗,更具社会学和人性意义吗?
于是,我写了《天知道》。主人公祈天是一家医药研究所的保卫科长——这个身份俗套了,侦探小说的罪犯常常监守自盗,但是这没关系,有些俗套其实是小说规律——祈天杀了一个人,放了一把火,他杀掉的是研究所首席艾滋病防治研究专家,烧掉的是这个专家即将成功的艾滋病研究成果。这是案件的侦破结果,铁证如山。他为什么杀人?因为他的家庭,他的妻子出轨了,而且他认为出轨的对象就是这个科研专家。至于为什么要放火,倒不纯粹是为了毁尸灭迹,他真正要毁去的,是艾滋病防治成果。只有杀人放火一起干,他才能把这项成果彻底从地球上抹掉。因为他认为,性病是上天对人类的善意提醒,而艾滋病则是上天的最后警告。如果艾滋病都可以预防和治疗了,那人类将从此肆无忌惮,最终在性泛滥中灭亡。天将降大任,所以他必须出手!这是一个狂人,他的狂,肇始于家庭,又以天下为己任。《天知道》写的就是这么个故事。
因为他是研究所的保卫科长,他可以在破案过程中一直出现;因为他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婚姻和家庭生活自然可以多用笔墨,而不至于写多了就让读者起疑,过快看破谜底。我的障眼法几乎可以一直用到小说最后。我一直认为,小说必须好看,不可以借艺术的名义沉闷和乏味。我相信《天知道》是精彩的,哪怕有人因为它穿了一件侦探小说的外衣而把它归入通俗之列。
何平:《天知道》的实践可能还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涉及到你对小说文体的理解。中国传统的小说是很“俗”气的,但现代小说被新派知识分子接过来之后越来越“脱俗”。
朱辉:小说之“小”,就在于它应该立足于“小”。凌空蹈虚的宏大叙事弄不好就违背了小说的本性。历史书写常常只剩下大人物,似乎是他们推动了时代的车轮,但是,在小说家看来,所谓大人物,其实也是普通人,他也“食色性也”,他也会爱恨情仇,也会因吃醋而冲冠一怒,也会为了博女人一笑而烽火戏诸侯,他当然也会吃坏肚子,甚至也会生脚气。人生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人人无所遁。小说家其实是小人物,千万别觉得自己了不得,是个大家伙,那是很可笑的。小事情吹吹牛可以,但在写作上,断不可自吹,把自己吹成皮筏子,以为就是普度众生的渡船。
即使是那些大气象的作品,举凡雨果、左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也还是立足于普通的人。正因为他们写了普通人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的表现,写好了人的喜怒哀乐,表现了人的普遍情怀和独特体验,我们才把目光投向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红楼梦》有三层,第一层是家庭生活和男女情感,第二层是家族败落,第三层是一僧一道和青埂峰。最文学的,恐怕还是第一层,宝黛恋爱,人情世故和大家庭里的勾心斗角,这是小说的质地,粗布还是致密的绸缎,一望可知;家族败落或朝代衰亡,那是衣服的款式,若布料不行,款式再高大上,也是假大空,纸糊的;僧道之类,到底对不对,恐怕读书人并不太计较。可惜很多当代作品,一味高屋建瓴,气吞万里的样子,但质地较差,更有趣的是,不少作品,所涉史实压根就是假的、错的,这样的东西只有娱乐意义,或者是用于交换的商品。
小说之俗,在我看来也是它的根本属性。没有疑议的是,中国传统小说就是俗的。大量的演义类小说,天生一付俗相,另外的小说,骨子里也俗。他们本就是为俗众准备的,以至于作者都不好意思署名。西方的传统名著,基本也是俗的,只是到了所谓现代和后现代,西方小说才“雅”起来,就是说,抽象了,变形了,虚了。这其实与西方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哲学和美术,强势切入了文学。就漫长的文学史来说,其实也才是新近的事情。我无意贬低谁,但是,“脱俗”肯定不能脱掉人气、烟火气。俗是一路,雅是一路,俗中有雅也是一路,且走着看吧。
何平:在最近的一篇评论里我把你的小说放在中国“世情小说”谱系上来观察。这个观点二十年前何志云谈你的小说就说过,他认为你“分外敏感的不是金戈铁马,而是民间俗众。”现在看,这个判断不但在当时是准确的,以此往后二十年至今,你敏感的依然是“民间俗众”。
朱辉:我在长篇《我的表情》的自序里说:“这部书是给一部分人准备的。如果你追求金戈铁马,漫卷红旗,那你不要打开它。它的伴侣应该是一杯茶,一支烟,柔和的台灯笼罩着你。”何志云先生的判断,记得是在我的第一个短篇集的序里说的,那时离《我的表情》还有十年。我会保持对民间俗众的关切和注视,因为我骨子里也是俗众之一。
何平:你并不是一开始就意识到俗世间对你写作的意义,你对俗世间文学意义的发现应该是从1990年代中期的《暗红与枯白》前后开始的。《暗红与枯白》是你的整个写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和新的起点。物欲对俗世间的规训,我们在你的《七层宝塔》依然能够感觉到《暗红与枯白》的余响。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一厢情愿的想象和过度阐释,你自己怎么看《暗红与枯白》对你写作的意义?
朱辉:感谢你对《暗红与枯白》《七层宝塔》之间隐秘关联的发现。很感谢。它们之间隔了整整20年。
《暗红与枯白》是我的家族史片段,是我心里流出的血。不知道别人能否想象,一个男人,长房长孙,在娶妻生子的年龄,对自己的来路和血缘那种特别的疼痛。至今我仍偏爱这个短篇,如果它还有缺点,恐怕是它蕴藏的情感太强烈了。其实此后,我从未忽略我的故乡。从《看蛇展去》《大河》《红花地》,一直到最近的《阿青与小白》《七层宝塔》,它们形成了我小说的另一个谱系。我出生在江苏兴化的一个小镇,它近几十年的变迁,它的风俗和人事,它在城乡变迁中的巨大变化,我了然于胸。我的亲戚朋友中,有很多阿虎那样的人,他们聪明、勤劳,鬼点子多,在每个新事物、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时,他们都能追潮逐浪。但是,他们从青年直到老年,往往也就忙的个嘴——为嘴忙。风俗人情,也基本是跟着物质在走。《暗红与枯白》写的是我不知道从哪里来;《七层宝塔》涉及了不知道往哪里去。
何平:虽然你是从“故乡事”开始了你的小说创作,但你写得最多的是当代城市非常态的性爱传奇。从早期小说的《游刃》《动静》《对方》已见端倪,而新世纪之后的《和辛夷在一起的星期三》《郎情妾意》《阿青与小白》《然后果然》《加里曼丹》《要你好看》《夜晚面对黄昏》《吐字表演》等等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性爱的浮世绘。我知道你写性爱最终目的是勘探时代洪流中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畸变及其诸种症候。
朱辉:我曾接受过一个记者的访谈,说了不少,最后发表出来的题目是她加的——《我对关系最为着迷》,这有点耸人听闻,会引起误解,但我承认,访谈的文字,是我的意思。我说的“关系”,涵括了各种各样的关系,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和环境的关系、人与物品的关系等等。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中,某人才成为这个人。当然,所有的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最为复杂,最为迷人,而且,具有概括力。哪怕你坐一张沙发,那沙发也是人做出来的,制造者聪明、体贴或者贪婪克扣,都通过沙发与坐者连接。
人与人的关系,若远若近,若还若往,是动态的,是小说文本里诡魅的舞步。写好人与人的关系,是小说家的天赋义务。这个世界上,人的分类有多种方式,历史上有个昏君说,天下除了我生的和生我的,都能睡,他这是按照可不可以啪啪啪为划分标准,我注意到,所有的划分方式中,把人分成男人和女人,是最直观也最简便的,老天已经代我们分好了——雌雄同体者是另一个话题。
两性关系伴随人类始终,纠缠于人的一生,而且常常必然接受现实世界的投射,这是我的敏感点。
3 科学思维对我而言已成为习惯。我认为,小说是人之理,而物理包含着更入骨的人情。
何平:如果我们意识到你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当代问题敏感和介入意识的作家,也许就能理解你为什么这么迷恋书写当代城市性爱传奇,因为在一个剧变的转型时代,性爱成为时代问题和人性的众水汇流之处,这是抵达我们时代和人性深刻的幽深秘径。
朱辉:人始终被欲望驱动,也许只有自杀的人,才有资格说自己已生无可恋。性既是本能,又附丽了很多本能以外的东西。也许我们不能说,只有写好了性和爱,才算写好了小说,但是,写不好性和爱,大概小说是有黑洞的。
在当下,都市的性和爱更为丰饶复杂。古人有句话,“奸近杀”,意思是不伦的性爱离凶杀已经很近。现实的案例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极端的情爱状态,更多的不那么极端的、隐秘的、被城市的灯火所遮蔽的情爱,这些不嚣张的情爱,确实是小说家表达城市的一个个端口。
何平:或者,一个时代人性畸变归根到底是人和人的关系,是人伦秩序的重新洗牌,这也是我们几乎所有焦虑和痛苦之源。基于此,你自然不会把人伦秩序简单理解为性爱,所以你要写《绝对星等》《七层宝塔》这样更辽阔开去、涉及更多人更多关系的小说。
朱辉:我的认知基础是:作为小说家我重视“关系”。“关系”包含人际关系,也包括人与物、人与环境、人与时间等关系。《绝对星等》《七层宝塔》诸篇,其实主轴是时间,是社会的变迁。《绝对相等》和《七层宝塔》是前后手写的。人这一辈子,顶着星空,踏着土地,最后灵魂飘于天际,身体委于泥土,其实都生活在小得可怜的一点时空中,这恐怕是人的终极恐惧。我希望小说也能大起来。所以我既有极小的小说,如《要你好看》之类,也有显现人的时空背景的小说,人活在时光之矢中的小说,《绝对星等》就是。
何平:你有一篇小说的题目是《暗夜危行》,你的每一篇小说都存在着躲藏在暗处、无法预知的危险时刻。你小说有阴阳两面,阳面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人民大众的起居注”,在这一面,你总有一种获取他者生活并精确书写的能力。除了你熟悉的大学和编辑生活,你写过洗头房和工地的农民工、拾荒者、医院代检员、艳遇者、播音员、政府公务员,以及城市其他形形色色的庸常者。对一个小说家而言,写出这些人物看得见的阳面并不困难,公共性知识加上对知识的想象性重构而成“起居注”式的日常生活就可以实现。而阴面,一个基本的常识,小说人物是一个典型,同时也带动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并建立一个自足的秩序化世界,这就是每一个人的“暗夜危行”。研究你小说的阴阳两面其意义不只在重建你小说的叙事逻辑,我以为这关乎你的小说美学和世界观,以你的眼光看世界是“危机四伏”。
朱辉:我是个“不安全感”很强的人。社会和自身都有显然的不确定性,不确定会导致疑虑。人又是很复杂的,如果只愿意看“阳面”,新闻报道基本就可以满足要求,但小说之所以可以长存(哪怕改头换面后的长存),其真正原因,正是它擅长表现“阴面”。我坚信,人的内心世界,比他的表情要丰富N倍。说出来的,只是想到的百分之一;做出来的,只是说出来的百分之一。如果我们要画一个蛋,只画阳面,基本就是一个椭圆,简直难以分清是鸭蛋或是鸡蛋,这时候需要测光、背光,需要顶灯,甚至需要X光,因为蛋里没准藏着小鸡哩。
何平:在当下的小说家中,你在小说结构上是有想法的,也许是出于理工科的教育背景,你的小说特别讲究“技术”,所以我说你是精准现实主义。这里面,理工科、社会科学和人文的不同教育背景可能还是存在着差异的。
朱辉:感谢你的“精准现实主义”。我虽是被逼无奈才学的工科,但我学得还不错,这说明了在理性思维上,我可雕,非朽木。我学的是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比一般的建筑工程结构更为复杂。我学过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学等一系列课程,所有的建筑,都需要计算,哪怕是最简单的楼房,它的结构、钢筋排布和粗细,混凝土的标号和配比,都有苛刻的要求。再怪诞、艺术的建筑,我基本上也能判断它的内在的结构和受力情况。所以我曾说过小说要有“腰眼”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定向爆破,作为专业的“破坏者”,他们一定洞悉结构,他们要找的是最薄弱的环节,是建筑的“腰眼”。
我很乐意承认科学训练对我思维的影响。这使我所操的文学工具,除了大刀阔斧,除了细针密线,还多了手术刀。科学让我明白很多事不可以想当然,没那么简单。譬如,水平如镜,是生活常识,但是我学过《水力学》和《水文水利计算》,这些学科告诉我,在一座阻水的大坝上游,水面决不是平的。因为水流被顶住,上游几十公里甚至几百公里,水面实际上呈现一个曲面。你要建设一个大坝,你必须精确计算出水面线,上游将有哪些地方会被淹没,那地方的居民就要迁居移民。这可是很大的事,是社会性的巨大问题,也是文学题材。宜兴那里有一把巨大的茶壶,凌空蹈虚,悬在广场上,茶壶微倾,壶嘴源源不断地流水,那已经成了奇观一景:为什么它凌空而又长流水?我几乎是一眼就看出了端底:那下流的水柱一定是一个支撑,而且一定是一根空心钢管,它从下面抽水,水到壶内后,再沿水管外面往下流——这是一个循环,所以源源不绝,流水正好隐藏了支撑的钢管……科学思维对我而言已成为习惯。我认为,小说是人之理,而物理包含着更入骨的人情。
(何平,著名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