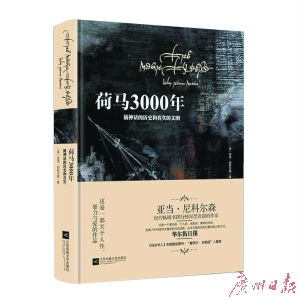
《荷马3000年》【英】亚当·尼科尔森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林颐
《荷马史诗》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它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影响极其深远。英国历史作家亚当·尼科尔森以《荷马3000年》重新诠释荷马,从初遇荷马、领会荷马、爱上荷马、探寻荷马……直到最后再思荷马,全书总共十二章,既是作者的心灵追索过程,更是一趟别具特色的西方文化之旅,让读者充分领略荷马史诗的珍贵价值。
《荷马史诗》形成了一种典型的西方式叙述技巧,即在作品中安排一个事件,构建一个寓言或者一个主干情节。习惯这一类型的读者不仅会对文学作品有着特定的期待,还喜欢将所有的情节按照自己的感觉进行预设。尼科尔森列举了许多译本对比,细致地剖析史诗的写作规律。英国诗人蒲柏将荷马带到了英语世界,就像一场激烈的文学风潮席卷了济慈和雪莱等人,济慈的诗风因此产生变化而被称为“伦敦腔的荷马”。但尼科尔森认为,蒲柏译本过于注重形式,为了叙事的优雅而牺牲了真实,反而破坏了史诗的本来面目和完整性。
荷马以一种难以想象的强度展现了战争的惨烈。尼科尔森说,“杀戮是《荷马史诗》的真相”,这个真相中包裹着深沉的叹息。《伊利亚特》中,我们目睹了阿喀琉斯的一切:最初的怒火中烧,盛怒难消,他的专断决绝,他最后克服冲动,陷入无尽的悲痛。直到全诗最末一卷,面对赫克托耳老父普里阿摩斯的痛苦时,阿喀琉斯放下了他的敌意来盛情款待老人。阿喀琉斯站在对手的视角来审视自己,人类在同理心的召唤中获得了共情,仇恨消逝,善战胜了恶。
但是,如果将荷马史诗仅仅理解为反战诗歌,这是小看荷马了。英雄的生命激烈、壮丽,却转瞬即逝,荷马史诗对死亡的关注远远超过对战斗的关注。书中,尼科尔森的个人经历犹如副线,与史诗的主线相交叉,让我们体会到史诗是如何进入个体的思维。
《荷马史诗》从来就不是神圣的作品。荷马史诗里的神也软弱、也卑鄙,也会犯各种错误,在神祇遍地的时代,人却是荷马作品的主角。自《荷马史诗》以来,希腊以及欧洲的传统都习惯于要求高水平的作品要具有相应强烈的、处于高位的道德方向,这也是通过《荷马史诗》实现的。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