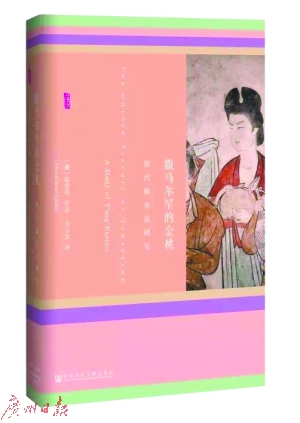
《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 (美)薛爱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宋 《牡丹图》 纨扇页
胡艳丽
“舶来品”是文化的信使,来自异域,因遥远而神秘,因稀缺而珍贵。《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为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先生在研究众多史料、文献,结合历史考辨,运用比较学知识,写成的一部涵盖唐代众多舶来物品,对当时社会文化进行深入探析的一部恢宏巨著。
这里的“舶来品”,既包括有生命的人、鸟兽及植物,也包括没有生命,但有故事的木材、食物、香料、药品、纺织品、宝石、金属制品及器物等。他们有的融入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有的泯灭于历史时空当中。一本来自西方的学术专著,除了为各种舶来品作了家谱传记外,也为我们洞开了第三只看世界、看自身的眼睛。
大唐对外来文化的情感是复杂的,既有藐睨天下的傲慢,也有对遥远神秘国度的向往,既有对“胡”、“蛮”的鄙夷,也有对奇珍异品的渴望。书中关于人的叙述,在热闹背后往往是荒凉。在那些外来质子、乐师、舞女、奴隶的背后,分明是一段段因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实力而产生的个体命运悲歌。他(她)们远路而来,有的是因其自身担负的家国使命,而有的成为了为政治献祭的牺牲品,还有些分明是在经济的魔爪下,被倒卖至大唐的无辜者。历史不会因任何人的眼泪和不幸而停止奔流的脚步,因这些舶来的人的影响,大唐的星空下,多了来自异域的神秘气息,文化也悄然发生了融合演变。“胡旋女”的身影犹在书中回旋,唐太子身穿胡服,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的场面,依稀再现,唐人、胡、蛮的身影渐渐出现重合。
伴随家国命运的交响曲,一批动物、植物,也开启了盛世中的文化巡游之旅。它们的命运,亦同人的命运般,在异国他乡生死难料。来自撒马尔罕的金黄灿烂的金桃,成了皇家的专宠,树苗栽种在皇家的果园里,象征着威仪的皇权。但遗憾的是,这种金桃并没有在大唐的土地上扎下根。书中这样的示例不在少数。不论是动植物,还是文化,关入重门其命运只有死亡一途,而放之到广阔的“田野丛林”,在自然的生态环境中,它们总会溢出灿烂的生命枝条。
每一种物品引进的背后,必定有一种称为“文化”的东西随之而来。比如从异国引进器乐,必然伴随异国乐师、音乐的相伴而来,异国器物的引进,往往伴随生活习俗的悄然变迁,异国的宝石、药物也会引起人们关于精神信仰的联想。每一件物品上面,都有其自身的文化符号,来自异域的魅力更容易吸引世人的注意,欣赏、模仿,甚至传承发展,这点在药物、金属制品,以及各种宗教及世俗器物方面表现尤为明显。
每一种文化都有滋养其成长的根系,但真正“血统纯正”的文化,其生命力往往是有限的,或消逝于历史的变迁中,或因所属族群的衰落而从此绝迹,那种广泛与外界融通,令自己不断成长、发育的文化,总能在求新求变中枝叶繁茂。大唐文化复杂多元,兼收了当时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在这场亦悲亦喜、历时百余年的文化大交流、大巡游中,包括大唐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实现了自身文化的再发育。
需要注意的是,万国来朝,万物来朝,天下齐珍荟萃于大唐盛世,一方面彰显了一个盛极一时的大国威仪,但另一方面不断暗长的奢靡之风,各种晦涩不明的政治暗语,也将这个庞大的帝国,送入了盛极而衰的历史轨迹。在极盛之时保持谨慎,在物质丰盈之时保持勤俭,在万众仰慕之时不忘修身养德,这是一个国家保持长盛不衰的前提。这也恰是纷繁的舶来物品,在带给中国丰富的文化资产的同时,送来的历史启示。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