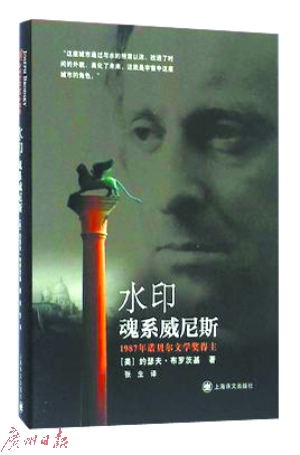
《水印:魂系威尼斯》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 上海译文出版社

南宋 李嵩 《花篮图页》
胡艳丽
威尼斯,一座自恋的城市。她被水连接、环抱,加之建筑、绘画、雕塑、歌剧人文荟萃,令她散发出迷人的气质,宁静中光彩荡漾。她自然也成为世界众多知名艺术家、文学家寄情的最佳场景。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茨基在他这朝思暮想的情人怀里“醉”了十七年,这是他逃离“前生”的重围,休养生息的所在。《水印》便是布罗茨基写给威尼斯的情书。这本书他写得相当任性,在这里他不需要深邃的哲思,亦不需要强迫自己写出精妙的诗句,他任凭这梦的伊甸园,把心灵转化为水银合金(书中代指镜子)。对于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国读者来说,读这样一本书,绝不是安然地享受,异域的词汇、文化,再加上作者的任性,翻译过程中原著“像素”的遗失,足够将读者弄得一头雾水。要想理解他的情感,理解他对威尼斯情人般的依恋,还需回溯他的“前世今生”。
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年生于列宁格勒犹太人家庭,少年时因对正规教育不满而退学,后从事过多种艰苦工作,青年时期因诗起祸,两次被送进监狱的精神病科,后以所谓的“过社会寄生虫生活”被判服刑,引起国内外强烈抗议,出狱后几经辗转又被驱逐出境,后入美国籍,斩获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多项文学大奖。
在书中,布罗茨基对其在母国的经历称为“前世”,而脱离之后的生活才是“今生”,“为了拥有另一种人生,我们应该结束第一种人生,而且这个活应该处理得干净利落”。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演说词里他说“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是一段漫长曲折的路程。可是对于持我这一职业的人来说,所谓两点之间的直线长度最短的公理早已失去了它的魅力,地理能为诗歌伸张正义。”
在书中,他用散文的形式延伸了诗歌的意象,坦诚了一个人的正常情感,以及独立自醒的意识。他以一种散漫的状态,借威尼斯的梦和水波,为自己疗伤。
威尼斯的水、威尼斯的城将他揽入怀中,冰冻海藻的气味令他神魂颠倒,接引者的美貌令他心旷神怡,他全身心地沉醉于被水波抱着、哄着、摇曳的城市之中。他甚至感觉完全是到了乡下,抵达了不可知的、没有意义的地点,甚或他希望这里就是他生命的原点,他的出生地。在这里,所有的故事都是配角,所有的过往都是尘埃,唯一不变的就是美,以及如消音壁般的吸附愤怒躁动,消化委屈,也消化雄心壮志的城市特质。威尼斯仿如布罗茨基生命中的一个渡口,连缀起了他的前世今生,连缀起了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之间的路程。
布罗茨基在威尼斯时而清醒,时而迷糊。他清醒时把威尼斯的石狮子想象成比天马更有文化的生物,因为爪子总比蹄子翻书更灵活,他说这里所有的怪兽,都承载着生物进化的记忆,它们是我们的自画像。他糊涂时便将自己交付给威尼斯的迷宫,分不清自己是在追寻一个目标,还是在逃避自己,是猎人还是猎物。在半梦半醒之间他享用着最好的威尼斯,分不清城与人,人与城的区别。清醒也好,糊涂也罢,在这美轮美奂,如同翡翠一般的城市中,人的思想、理性、正义都可以和感观一起休养生息。
“这座城市通过与水的相濡以沫,改进了时间的外貌,美化了未来。”威尼斯是上帝唯美的眼泪,给予世人一个可以暧昧、可以休养、可以沉醉的场所,她收留的是人的灵魂,而献出的是如梦如幻的人间仙境以及伸张正义的人间诗意。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