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雪涛:介入时代唯一的方法, 就是把小说写得像点样子
“即便把作者的姓名隐去,也能轻易或相对轻易辨认出到底是否是你的作品。”青年评论家李德南的这句评价,充分肯定了作家双雪涛的写作辨识度。对于任何一个有志于将文学作为终身事业的人来说,这都可以算是写作的终极目标之一。双雪涛作品中冷峭直白的语言,套盒般的结构,磨碎融入在字里行间的观念表达,让这个新锐从一开始就从大量写作者中脱颖而出。
称双雪涛为新锐,是因为他2010年才开始写作,但一出手似乎就有武林高手的气质。短短几年内,他连获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小说奖、“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入围第十四届台北文学奖年金奖,并陆续在《收获》《上海文学》《文学界》等刊物上发表作品。
从事写作之前,双雪涛是一名银行职员,业余时间给杂志写点影评。直到他看到作家王安忆的《小说家的十三堂课》中讲到“小说是用现实材料搭成的另一个世界”,受到启发的他决定开始搭建一个“完全幻想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校园生活青春记述,有玄幻传奇和民间人物,也有对现实生活的观照。
双雪涛的写作成长速度很快,评论者们盛赞他的天赋,然而阅读和生活经验的积累于他同样重要。从区图书馆到市图书馆,他完成了自己最初也最终深植于他写作中的积淀:大仲马、雨果让他学会阅读,更重要的是:“我仔细读了张爱玲,汪曾祺,白先勇,阿城,看他们怎么揉捏语言,结构意境,仔细读了余华,苏童,王朔,马原,看他们怎么上接传统,外学西人,自明道路。”无疑,似乎已经远去的先锋文学对双雪涛的影响很大。“在文学自身之内实现文学的精神”,这是他对先锋精神的继承。
李德南是第一个给双雪涛写评论的人,他说双雪涛“有着小说家的狡黠与智慧,用烟雾迷蒙你的双眼,看似是在一本正经地给你讲一个故事,陈述某个观念,其实他真正重视的,是另一个,是藏在水面下的那一个”。双雪涛永远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故事,内心的锋刃让他的小说中存在着某些执念,关于人的自由和尊严,关于社会中的某些现象和问题,他的思考与困惑都由小说曲折地呈现,而又不提供定见。
最近,双雪涛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和长篇小说《聋哑时代》,用他的话来说,他正在用小说的方式,来摸到“更大的东西的裙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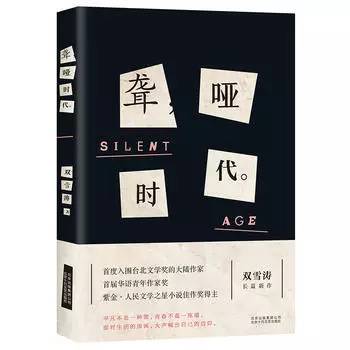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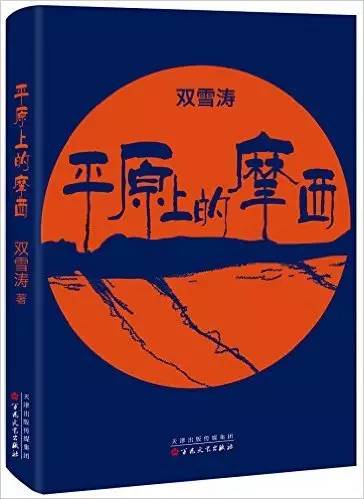

双雪涛
写作本身就是写语言,需要具备抓住语言的能力
记 者:我想从你和李德南近期那个对话谈起。在这个对话中,你提到,如果没有先锋文学,没有那一代作家,你是不可能写作的。其实从你最为人们熟悉也最受好评的《平原上的摩西》里,可以看出,先锋作家信奉的叙事和语言,对你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先锋文学给了你什么样的影响?
双雪涛:
先锋文学对我的影响确实很大,这里面也包含了我接触到先锋文学的时候是高中时代,正是走向成人世界,且带着某种利刺和执着的年龄,这可能与先锋文学的精神比较契合。另一方面我有时候只是因为方便,所以屈从于“先锋文学”这个词汇,而这个词汇的内涵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有搞清楚,我想包括余华在内的那批先锋文学作家也并不愿意一生都与这个词汇相连。以我个人的理解,也许这个词指的是某种探索的精神,某种在文学之内实现文学的精神,某种自私地表达自己的精神,可能就是这种精神一直影响着我,提醒我,文学本身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如同一个数学定理即使在几百年内无法得以应用,它的意义也是重大的,它说明它本身。
记 者:以《平原上的摩西》为例,以此来解剖你小说写作的一个横截面。一个侦察案件,多个人物的第一人称叙述,各个故事交缠,几个时间在各个故事间的纵深。在我看来,这样的结构是你精心设计的,这个结构层次复杂,多条走廊交叉又通向一个你预设的目标。你似乎喜欢复杂结构,这是否与你所说的小说的“密度”相关?
双雪涛:我也写过简单的故事,或者说不怎么有故事的故事,比如《跛人》,比如《走出格勒》。《平原上的摩西》是我小说中故事性比较强的,首先是它的篇幅,在中篇小说我愿意营造故事,营造也许不准确,我愿意把故事放置进去,但是其实我在写之前并没有怎么构思故事,我还是跟短篇小说一样从一个感觉开始,有个大概的模糊的方向,然后被叙述带动,去捕捉故事。《平原上的摩西》这部小说因为我想说的事情有一定的跨度,也因为里面镶嵌了案件,所以故事性和通俗性强一些,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写的这些人物本身有故事,这是一群有故事的人,所以我可能还是在写人,在叙述一个东西,故事是随之而来的,如果细读了这个小说会发现,它的故事并没有明确的结局,中间也缺失很多东西,也许正是这些东西,使它成为了一篇小说。
记 者:更进一步,我好奇你怎样处理细节,在如此复杂硬实的结构里?我有一点感觉,其实你的细节有时候会让小说的空间留出来,小说虽然密度很大,却仍然有让人呼吸的口子,某种程度上,也让结构不至于框住。
双雪涛: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其实我在上一个问题已经回答了一半。实话说,有些缺口是因为没有必要写,有些缺口是因为我写不了。所以不能说每一个设计都是设计的结果,有时候是避重就轻,依靠了巧劲。托尔斯泰是不会这么干的。
记 者:回到语言,某种程度上来说,你的语言比起结构来说直白许多,但在这之外,更重要的是你语言的精炼、紧致,一种说法是“北风般的冷峭”,你说这可能与你曾经做过银行职员相关,所以追求有效叙述,同时也是你希望言简意赅的美学取向。
双雪涛:语言这个东西,我的追求是写我自己看着舒服的语言。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直白的语言,但是我认为我在使用书面语工作,这种书面语我自己摸索了一段时间,在一些短篇小说里使用过,从2015年开始,稳定了一些。我不太喜欢在语言上追求新奇和怪诞,好像一栋有太多弯角的房子,我也不太喜欢不把语言当回事儿,美其名曰语言要透明,语言要是透明了,那小说本身可能也就不剩什么东西了。我习惯于一种自然但是其实推敲过的语言,一种从作家的本性和创作实践里生长出的语言。写作本身就是写语言,信手拈来,这种信手拈来的基础是,本身你已经具备抓住语言的能力。
一个作品的复杂程度,是自然携带的
记 者:《平原上的摩西》这本小说集收录你的一些短篇和中篇。里面有一部分是青春记忆的写作,包括刚出版的长篇《聋哑时代》同样是讲述“80后”的成长。但你的“80后”成长主题的写作有一点特别的是,你不仅仅在讲述“安娜”、“安德烈”和“我”们,更多的是在讲述这一代生活着的现实。这部分“80后”青春记忆与成长的写作你想表达些什么呢?
双雪涛:首先我觉得我并没有长大,我也觉得没有几个人长大了,后半句可能有点武断,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所谓的成年人其实并不怎么存在,这是一个人类自己对自己的误会。还有一点是,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是无声无息地长大了,而且很多人会非常轻易地遗忘自己的苦难,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跟上一代人比,我们的苦难是挺渺小的,甚至是挺可笑的。但是我并不这么觉得,我一直认为我们损坏过,有的人后来好了,有的人一直没好。我没有那么自负,想要代言别人,我只能代言我自己,而就我自己而言,我觉得我不想遗忘我童年和少年的故事,那也许是一些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对我而言,甚至对我的未来而言,都极为重要。所以我可能不算是书写青春记忆,我现在还在这青春之中。
记 者:在与张悦然关于《平原上的摩西》的对话中,你曾经说,你的写作有一个向上回游的过程,也就是说从自己到父辈。这篇小说里的“傅东心”带有你父亲的一点影子,她是你对上一代人理解的某一种缩影。“我觉得那代人是有力量的,即使是沉默的,比我们要有生命力,比我们笃定……我们以为我们是有那么一点反抗精神的一代,其实我们非常平庸温顺……”你这样的表述其实很有意思,或者说我对此也有认同——父辈不是我们曾经以为的那样,他们的力量藏在深处,又不经意显现在外。
双雪涛:我们的父辈成长于疯狂的年代,当然他们成人后的年代也一直挺疯狂,所以他们应该说是经历了非常魔幻的一生,他们可能在少年时被发配到村庄去种地,现在则热衷于同学聚会洗温泉。只要动脑想一下,就觉得他们的生命体验是非常跌宕的,猝不及防的。他们有兄弟姐妹,我是没有的,他们也许也有过信仰,我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比我们更真实,当然这个“他们”是我对于我所认识的有限的“他们”的概括。我们有时候可能需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到底真的关心这个世界吗?关心周围的人吗?我们的爱与恨,成色充足吗?有时候我会觉得我的父母他们的脚是站在地上的,而我们是漂浮的,笑嘻嘻的,轻便的。
记 者:李德南说你“将自己的观念磨碎,融入字里行间,看似是在一本正经地讲故事,陈述某个观念,其实他真正重视的,是另一个,是藏在水面下的那一个”。我不知道他这样的评价你认不认同,但在我直观的感受里,你的观念是必须仔细琢磨才能触摸到一二的,这或许是你设置复杂结构的一种原因。但我想请你谈谈这水上的和藏在水面下的另一个之间,你是如何处置的?
双雪涛:德南是一个非常敏锐的批评家,他的解读我非常喜欢。就我自己而言,我写作时可能不会想太多,我一直觉得一个作品的复杂程度,可解读的空间,不是自己去营造的,而是自然携带的。我喜欢这个故事是这个形状,可能就是因为我喜欢,如果这里头有些东西可以探讨,那是阅读者的优秀,也是我比较幸运。
记 者:你重视小说介入现实、介入时代的力量和功能,也说自己内里有些锋刃会显露在小说中。你希望如何用自己的小说叙述当下甚至以前的现实、故事?
双雪涛:我觉得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介入时代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小说写得像点样子,这点上我比较小家子气。如果我有点锋刃,那是我性格所致,我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要拿小说干吗?同时我可能也觉得,当你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自己也就这么点手艺的时候,也许能摸到一点更大的东西的裙尾。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