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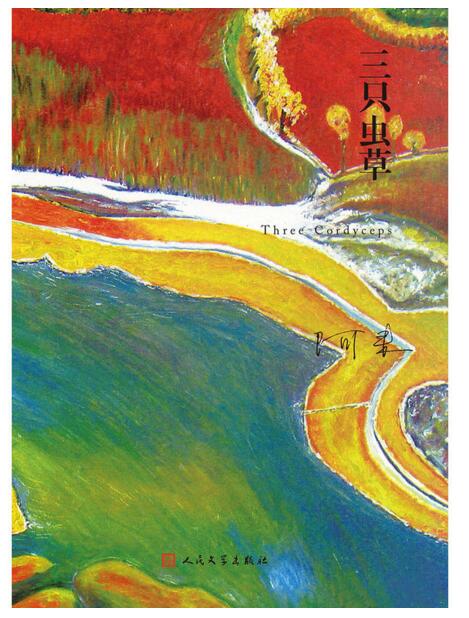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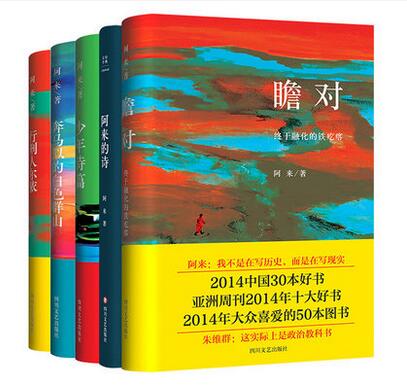
阿来圆脸、头发微卷、皮肤偏黑,眉头有一道眉心纹,紧蹙时愈发“深刻”。
11月26日,阿来与长沙读者的见面会持续了三个小时,他腰杆挺得笔直,一手拿着话筒,一手插在裤兜里,声音沉稳,像个严肃的乡镇干部。
一下讲台,脸上的肌肉松弛下来,“严肃”化开,表情开始丰富。我看着他红黑的脸问,“皮肤偏黑是经常在外跑晒的,还是天生的?”
“粉底打暗了。”他闪现一丝“坏笑”,见听者被逗笑,他补充说,“本来就挺黑的。”
这位历经放羊娃、水电站工人、拖拉机手、中学老师、文学编辑、《科幻世界》总编辑、社长等多重身份的茅盾文学奖最年轻的获奖者自称是“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他说,“人生发展如果不出轨一次,至少出一次‘意外’吧,要不然看别人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
“如果期待有点惊喜,应该是不计成本的”
如果按部就班,世界上可能会多一个校长阿来,而不是作家阿来。
作家阿来,是阿来人生中的一场“意外”。在阿来因《尘埃落定》名声震起的1998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这样描述自己的起点:我出生于一个二十多户人家的小山寨里,小村子的名字在我的一些小说里出现过:卡尔古,是山沟更深处的意思。你可以想象她有多么僻静遥远。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对于出生于小山寨,当过放羊娃、水电站工人、拖拉机手后,成为马尔康县一名中学老师的阿来而言,选择并不太多,因为“不同的时代对年轻人都有一个规定性,大部分人是沿着这条路去的。”
有一天,校长准备动员阿来了。阿来突然问了校长一句话:“校长,你现在多大了?”他说:“我56岁了,再过几年要退休了。”
“你是什么级别呢?”答:“相当一个副处长吧。”
“好难啊,好难啊。”阿来说,“如果所有一切都进展非常顺利的情况下,等我当校长的时候,大概也到你这个年纪了,当到校长也就退休了。”
“当你真正被人规定好人生里程的时候,你突然间就觉得人生特别没有意思,人生发展如果不出轨一次,至少意外出一次吧,要不然看别人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
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大概就只剩下写作这一行可以让我忘掉那个烦恼,这也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我产生意外的一件事情,所以一直做到了今天。”
“可是,走少有人走的路,是否考虑过最坏的情况?”我问。
“如果期待有点惊喜,有点预估之外的东西,我想应该是不计成本的,把所有风险评估都做完,可能就迈不出去那一步,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想法,后来就是做了太充分的风险评估,后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们这种人偏偏就是倔,你不回答我就来回答”
中专,是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迄今为止的最高学历。
他也并不准备去“拿”一个更高的学历。如果说,早年因条件所限,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后来,当同时代作家纷纷上作家班,拿本科或硕士学历时,“我发现我要拒绝这个东西,我不能被同质化。”
“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不是另一种幸运?”我问。
“是的,上了学,老师给一个标准答案,让我去考试,我想我不要这些东西。我们认识字,认识一定程度就获得阅读能力,就是一种学习能力。遇到问题,可以自己去寻找答案。”
渐渐地,阿来有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从何而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阿来做了长达四年的嘉绒藏族地区地方史的研究,搜集整理地方志、地方口碑材料,吸收采纳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土司制度的研究成果,从史料到现场,从现场到史料多次往返,思考的成果是一出炉就拿下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尘埃落定》,这部描写1950年以前藏区的小说,说的就是“我们从何而来”的故事,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1950年四川解放,上个世纪的百年刚好被分成了两半,一个是旧的藏区,一个是新的藏区。《尘埃落定》写的是1950年以前的藏区,接下来的小说《空山》写的就是新藏区。
“这一系列小说,归根结底,是不是都围绕的一个问题,即:我是谁?”我问。
“可以这么说,既是我是谁,更重要的是,我们是谁?文学的特殊和普遍,就是单数变成复数的问题,就是‘我’变成‘我们’的问题。”
“我自己进行自我教育,面临的很多问题,现成的理论教科书还是官方的解释,都不能解决我们这些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大部分人就不管了,假装这种问题跟我无关,我们这种人偏偏就是倔强,你不回答我就来回答,这个世界上总要出现这样的人。”
“当官赚钱都不动心了,唯一没法超越的只有美女了”
“阿来老师,你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长沙的读者见面会后,一位女读者对他说。
“那我应该是什么样子?”阿来反问。
“应该超尘脱俗一点,而不是现在这样。”她说。
阿来笑,没有作答,手指缝里的烟头烟雾缭绕。
今年57岁的他,早已不是文艺书生的长相,身材已发福,演讲间隙会溜到门外,抽一支烟,然后再回来。
他绝不是甘心于埋头故纸堆的书生,他想做点事,曾将十年光阴给了《科幻世界》,担任总编辑、社长等职务。
接待、应酬、交谈免不了,“会不会有很多委曲求全的时候?”我问。
他边给读者签名,头也不抬“满不在乎”地说,“商务谈判不是委曲求全,就是一个彼此妥协,讨价还价的过程。我们进入了任何一个行业都有规则,商业有商业的规则,在文学的场合就说文学的话。但我有我的底线,在商场,可以请我喝酒,但我不吃回扣,钱可以自己挣。”
“那你被欺骗和算计过么?”“太多了!”阿来答。
然而,在阿来最新的小说《三只虫草》中,主人公少年桑吉因为三只虫草,看见了一个充满着俗世物欲的“复杂”的成人世界,最终却没有被这个世界同化,依然保有人性的美好。
实际上,阿来将这部小说的写作,也视作自己的一场冒险,“桑吉能不能干干净净地回来,作者自己究竟敢不敢相信他,敢不敢相信这个社会当中还有一些美好和善良,不会在这个世俗社会中完全湮灭?这也是对自己内心还有没有残存这样一点星星之火的考验。但是我很骄傲地说,我都做到了。”
“但你是如何做到的?”我追问。
“我觉得有两个东西。第一是人格塑造,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知识分子的人格捍卫和塑造。但人格塑造之难就是因为社会不干净,要把你拖进去,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情怀理想重要的就在这儿。第二,我也研究纯粹宗教,宗教给人很强的宿命感。不管用什么手段得到的所有东西最后都会过去,我们腿一伸,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没有了。”
他说,常常有文学家特别介意学术界的评价,认为这是进不进文学史的问题。“我经常笑他们,再过20年,你腿一蹬,进不进文学史你根本不知道,重要的是参与的过程。”
“那么,再问一个世俗的问题,当别人欺骗你时,你会恨么?”
“几天会有,但不长久。”停顿片刻,他继续说,“而且我这种人后来也不太上当,因为没有多少祈求了,当官不动心,赚钱也不动心,基本上都超越了。”
最后,他恨铁不成钢的口气自语,“唯一没法超越的,只有美女了……”
潇湘晨报记者 赵颖慧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