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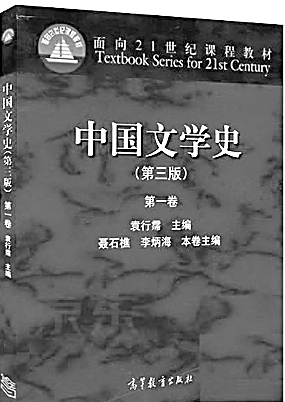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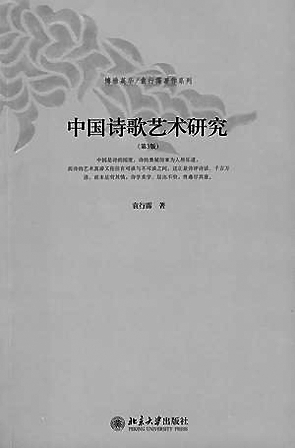

很早就想写点文字,表达对袁行霈先生的感念和敬意。可要说的太多,提起笔来一时不知从何讲起。
我曾在1984年本科毕业留校后被派到北京大学师从袁先生研修古代文学。第一次见到袁先生是在他新开的“唐宋词研究”课堂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的一句话。他说,研究古代文学一定要找人品和作品都要好的,人品不好还研究,那有什么意思?看似不经意,却道出了先生学品与人品兼修的治学原则。
先生视古人为同道,做学问不是向别人炫耀,而是为了增进个人学养。恰如孔子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记得先生的授课地点位于五四操场边上的101阶梯教室。那时,先生住在北大西门外蔚秀园27栋204“一担挑”两居室,我租住在西门外西苑操场2号一户农民家的四合院里,相距不远。
幸运的是,几乎每次下课,我都能陪先生一边往回走一边交谈,途经未名湖边的小路,绕过红楼,到北大西门外分手。从落叶缤纷的深秋到微雪初霁的冬天,一路走来。每当夕阳西下,拉长了我们师生身影的时候,是我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
30多年过去了,但与先生的交往永远定格在记忆中。我赞同有学者以“表里俱澄澈,心迹喜双清”来概括先生的人品和学品,但还可以再简练些。在我看来,先生的学品与人品一言以蔽之:“清”而已矣。先生把其自选集命名为《清思录》,可谓夫子自道。我以为“清逸、清拔、清远、清淳”是先生的治学特色,也是先生人格魅力所在。治学风格与人格修养那样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在当代学者中并不多见。如果结合中国古典学术的当代转型来考察,更能一睹先生的治学风范及其在当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 清 逸 /
在“艺术失语”下创建诗学话语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学术的黄金时代。从“十年禁锢”挣脱出来的中国学术在改革春风的沐浴下,开始回归学术本位,尊重学术规律已成为学界广泛的共识,并涌现出以《管锥编》为代表的开一代学风的巅峰之作。
袁先生此时正值盛年,面对来之不易的学术环境,经过冷静的思考,选择了一向被人忽视的诗歌艺术作为研究重点。
首先,选择诗歌艺术作为研究对象是文学回归艺术本位的时代要求。“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十年浩劫中,文学作品的艺术研究处于失语状态。袁先生从事诗歌艺术研究带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意义。
其次,选择诗歌艺术研究意味着选择了艰难。古人谈诗说艺,即兴感悟,点到为止,缺乏系统的分析。今人论诗在畅言和寡言之间,难言和尽言之间,欲打出一条诗艺的通道且保持诗的灵性与慧悟,绝非易事。先生选择的正是这种艰难。
第三,如何揭示诗歌的艺术奥秘?早在1978年,先生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倡导“横通”“纵通”的研究方法。横通,是将文学与哲学、政治、宗教、绘画、音乐等学科打通,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纵通,是对研究课题的来龙去脉要有纵向的把握,对局部的问题也要做历史的、系统的考察。二者结合,仿佛由横轴、纵轴组成的坐标,对古代诗歌艺术进行精准的把握,即博采,精鉴,深味,妙悟,以打开诗歌艺术的奥秘。
第四,建构中国特有的诗歌艺术批评话语体系。先生曾说,做学问如下围棋,虽然是举棋落子一步一步走,但胸中须有满盘全局的观念。博采精鉴也罢,深味妙悟也罢,横通纵通也罢,归根结底,是在具体分析中国古典诗歌作品的基础上通观周览,摸索出一套符合中国诗歌艺术创作与鉴赏规律的批评话语。
先生一方面从微观入手,分析屈原、陶渊明、谢灵运、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苏轼、周邦彦、陆游诗歌的艺术构成、文学渊源以及诗人人格对其风格形成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宏观着眼,系统阐述了中国古代诗歌语言的多义性,诗歌意象、意象群及意象组合方式,诗歌意境的构成、特征、深化、开拓和创新。
1987年结集出版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标志着中国诗歌艺术批评话语体系建构的初步完成,体现出鲜明的袁氏风格。先生提出诗歌从语言到意象、由意象到意境、由意境到风格到人格的系统分析方法,既传承了古代诗话的鲜活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情趣,又将古代诗论感悟式的评点发展为系统的艺术分析的方法,并得到了学界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奠定了先生的学术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先生建立系统的艺术批评方法得益于自身的才情和悟性。他幼承家学,渊源有自来,翰墨书香,耳濡目染。考取北京大学后,受业于著名诗人、学者林庚教授等名家门下,学业精进。
先生对文学艺术有极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和精准的把握力,这是源于长期浸润文学艺术所形成的慧悟。钱锺书说,“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先生是学者,也是文人,他以文人之灵机慧悟洞彻古人之说,他的古代诗歌论著及后来的《论诗绝句一百首》的创作,赋古典以新义,字里行间流露出一股清逸之气,随意挥洒,左右逢源,如惊蛰过后的万物萌动,如秋水长天上的鹜霞齐飞,含英咀华,清灵秀逸,舒卷自如。
葛晓音先生说,听袁老师讲课是一种艺术享受。在我看来,读先生的文章又何尝不是艺术享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如此,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末被程千帆先生誉为“提要钩玄,敲骨得髓之作”的《中国文学概论》又何尝不如此?
/ 清 拔 /
在“曰考曰证”中加强理论思考
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文革”期间相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古典学术在另一个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即国学研究的兴起,实证方法的提倡和学术规范的强化。大量关于作家生平、作品系年之类的杰出成果的出现,以及《全宋诗》等大型古籍整理出版,便是重要的标志。
从文学研究拓展为文献、文化研究,提倡有问必考,有疑必证,与20世纪80年代新锐的学术思潮相比,锋芒开始收敛,考据成为20世纪90年代主要的学术风尚。袁先生也从事考证工作,他的《〈山海经〉初探》《〈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陶渊明享年考辨》等文章证明了他在这方面的细心。但他更敏锐地开始了新的理论思考。
国学的兴起,以1992年北京大学成立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为标志,袁先生担任中心主任,并于1993年创办并主编了大型学术刊物《国学研究》。2000年,中心更名为国学研究院,先生任院长。
此后,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国学院,国学研究与普及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然而,这背后也出现了令人不无忧虑的两种倾向。一是对国学研究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二是问题意识的缺乏和对理论的忽视。
在这种情况下,袁先生开始谋划更大的学术布局,继构建以意象分析为特色的中国诗歌艺术批评与鉴赏理论后,又在以下领域有了新的理论开拓——
第一,撰写《中国文学概论》,试图从总体上对中国文学加以阐述。涵盖了各个时期、各种文体,提出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理论问题,如中国文学的特征,中国作家的地域分布等。该书上编总论中国文学的特点、类型、分期、传播和作家分布,下编分述各种文学体裁的渊源流变、风格特点。书中所列章节大都富有开拓性和启发性,形成了开阔的理论视野和隽永的诗意表达相结合的特点,用罗宗强先生的话说,“是一本在观念上和建构上都有所创造的文学史”。(《读书》1991年第8期)
第二,《中国诗学通论》(与孟二冬、丁放合著)突破以往的研究格局,以划时代诗学著作作为分期依据,把中国诗学史划分为六期,将中国诗学分为功利派和非功利派,并将中国诗学特点概括为实践性、直观性、趣味性三个方面。相对于以往的诗学史论著,有了很大的理论提升。
第三,主编《中国文学史》,体现了袁先生文学本位、史学思维和文化学视角相结合的文学史观。即以文学作品研究为核心,注重探索并描述文学发展变化的前因后果,寻绎“史”的规律,以文化学的视角考察文学,借助哲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心理学等邻近学科成果和研究方法,在学科交叉点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可以说,这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最有学术眼光和理论深度的文学史教材。
思想有多高,知识有多宽,决定学问走多远,学识决定学问。即使主张“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乾嘉朴学也同样有立足小学以通经明道的思想观念。戴震《戴东原集》卷二云:“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蹿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6页)思想观念对考证方法的引领不言而喻,而理论思想如果离开了严谨的资料支撑也会变得空洞空疏。
袁先生自谦自己是研究文学史的,理论素养不高。但从《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到《中国诗学通论》,从《中国文学概论》到《中国文学史》,他完成了从诗学到文学从概论到史论的拓展,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在“横通”“纵通”视野下对中国文学的感悟与思辨,对中国文学发展演变内在规律和外在成因的寻绎,是对中国文学特质与格局的通盘考量。
这种视野与格局,在以“曰考曰证”为学术时尚的氛围中显得清拔而超迈!一如岩上之劲松,一任西风烈烈,我自青翠挺拔;一如远山之奇峰,纵使云遮雾断,依然壁立峭拔。
文学之外,先生还有更为高远的学术追求——对中国文化、文明的通盘思考。
/ 清 远 /
在“文化馈赠”中敞开学术襟怀
进入21世纪,快速崛起的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引擎。经济大国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大国文化。中国古典学术正酝酿一次更大的学术转型,即朝着构建大国学术文化体系的方向迈进。构建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介绍中国经验,传播中国智慧,并与世界文化开展对话、交流和交融,已成为当下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社会担当。
继中国诗歌艺术、中国文学研究之后,袁先生又开始了新的学术征程。他把学术目光瞄向未来,致力于建构与大国经济相适应的中国古典学术当代价值与传播研究,开始打造高端学术平台,组织全国优秀专家、学者致力于中华文明史、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与传播,并取得了标志性成果。
一是编撰《中华文明史》。作为第一主编,袁先生贯穿其“文化馈赠”的理念,将中华文明和灿烂文化馈赠给世界。在他看来,中华文明的特色具有阴阳观念、人文精神、崇德尚群、中和之境和整体思维五大特点,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是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六点。该书将中华文明放到世界格局中考察,写出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前瞻性和启发性,从而在总结文明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启发读者思考未来文明的发展方向。可以说是一部浓缩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与经验并馈赠给世界的文明史。
二是成立北大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袁先生出任主任,将基地工作的重点放到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上,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如《中华文明史》四卷本出版以来,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在美国著名汉学家、华盛顿大学康达维教授主持下,历时5年译成英文本,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由稻畑耕一郎教授主持的日译本共八卷,也已于近期由日本潮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塞尔维亚文、韩文、俄文、匈牙利文译本,正在翻译中,明后年也将在各自国家出版。基地还编辑了《国际汉学研究通讯》,一方面介绍西方汉学研究前沿,一方面把国内研究状况介绍给海外汉学界,已经出版了12期。袁先生看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瓶颈是翻译水平,便安排基地于2014年举办“国际汉学翻译家大会”,加以推动。
三是主持中央文史研究馆编撰《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这又是一部多学科融合的大型学术著作,全国各地近千位专家学者历时8年通力合作完成。《通览》上溯文化源头,下迄辛亥革命,按我国的行政区划各省区市均有一卷,连同港澳台共34卷,大约1700万字。作为第一主编,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史有两个坐标:一个是时间的坐标,一个是地域的坐标。一方面,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有多个发源地,其发祥与兴盛的时间也有先后之别。特色与时间不尽相同的文化板块之间互相交错、移动,呈现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文化地图,编织成中国文化的全景。《通览》被认为是填补了我国全方位、多视角研究地域文化的空白,为中国绘制了首部大型的分省文化地图,也是一部肩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命的大型学术著作,体现了学术性、现实性和可读性的有机统一。
不用多举例,从文学研究到国学研究,从文化研究到文明研究,从历史意义上的“时”的研究到空间意义上的“地”的研究,从个人著述到集体书写,恰如汇百川而成汪洋,集风云而成气象,这一次次学术跨越和拓展,都与当代中国古典学术的递嬗同步,这种“同步”究竟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莫逆冥契”,还是某种意义上的引领和示范?这要交给未来回答。但可以肯定地说,贯穿始终的是先生以现代的眼光对传统文化经典、文化精神的执着守望,是对复兴传统优秀文化并传播于世界的自觉担当!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说:“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里的现实意义。”
/ 清 淳 /
在“守正出新”中彰显治学风范
如果说,“清逸”展现了先生的才华和气质,“清拔”展现了先生的学力和识见,“清远”展现了先生的襟怀和魄力的话,那么,“清淳”则集清逸清拔清远于一体,正所谓腹有文章气自华,豪华落尽见真淳也。先生在学界声名日著而心淡如菊,清雅淳厚成为其治学为人的又一重要特征。
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守正出新”。
何谓出新?先生说:“学术上的出新,无非体现在三个方面:或者有新的材料,或者有新的观点,或者有新的方法。做到其中的一个方面,就可以称为出新。”那么如何出新?先生说:“出新不能离开守正,基础要稳,走的路要平正通达。只要基础牢固,有充分的资料作依据,可以大胆提出新的结论。但为了求新而故意用偏锋,或者故意抬杠,则不是学者的风度。”
这里,先生提出“正”和“偏”两种出新方式,肯定前者不赞许后者。所谓“正”就是说要打好牢固的学术基础,勿求速成。正如韩愈所说,“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与之相反,剑走偏锋,追求捷径,心浮气躁,刻意求新或故意抬杠则不是学术研究应走的道路和应有的态度。
与“守正出新”相伴的是“以古为邻”。著名史学家张舜徽先生说,“吾与昔人近,吾离今人远”,道出了老一辈学者在动乱年代里逃避尘俗亲炙古人的优雅生活。
袁先生以古为邻的态度正如杜甫所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他喜欢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郁、王维的禅意,喜欢二王书法、宋元山水画,喜欢莫扎特的音乐、巴尔扎克的小说……当然,他最看重的是与他从小结伴如影随形朝夕相处的老朋友——陶渊明。
先生对陶渊明的研究可以说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小时候,他听到陶渊明的故事就找到陶诗来读,后来着手研究陶渊明时,便兼顾他的为人和作品两方面。先生自述,研究陶诗和整理陶集已不仅是一项研究工作,而且是一种精神寄托,是“我跟那位真率、朴实、潇洒、倔强而又不乏幽默感的诗人对话的渠道”。
先生用20年的时间写下了《陶渊明研究》和《陶渊明集笺注》两部厚重扎实的著作,集陶渊明研究之大成,达到了新的高度。从目录、版本、校勘、笺注,到生平的考订、史实的考证、艺术的分析,可以说将全部的知识储备都用上了。
在先生看来,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是士大夫精神上的家园,他为后代的士大夫筑起一个精神上的“巢”,一道精神上的“屏障”,使他们求得精神上的安宁。
此后欲罢不能,先生又写出《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和《古代绘画中的陶渊明》两篇长文,出版了《陶渊明影像》一书,从传播学的角度进一步探讨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提出“陶渊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的观点。
没有深刻的人生体验,没有对陶渊明其人其作的深切感悟,没有各门知识的融会贯通,是很难提出上述观点的。先生的陶渊明研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将会越来越得到尊重。
袁先生喜欢陶渊明的诗句:“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他认为,“做事不能不考虑功利,但功利主义不好,读书做学问尤其不能讲功利主义。追求和发现真理的过程是一种自我完善、自我满足的过程,快乐就在这个过程之中”。
坚持“守正出新”的理念就是坚守治学的雅正之路,从而避免学术上的急功近利;坚守陶渊明的古训就是要始终保持清雅淳厚的心态,进而成为抵御当下浮躁焦虑的一道屏障。
行文至此,我不由得又想起了30多年前的那一幕:上完课,我陪先生从五四操场边101教室走出,沿着未名湖畔小路边走边谈,绕过红楼,在通向西门的草坪上,夕阳余晖拉长了我们师生的身影……
2016年是袁先生八十华诞,祝先生学术青春永驻,生命之树常青!最后以一首小诗《未名湖畔行吟》来表达我的祝福——
道是无名胜有名,流觞曲水聚兰亭。
方塘半亩谁云小?跨海凭风掣大鲸!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