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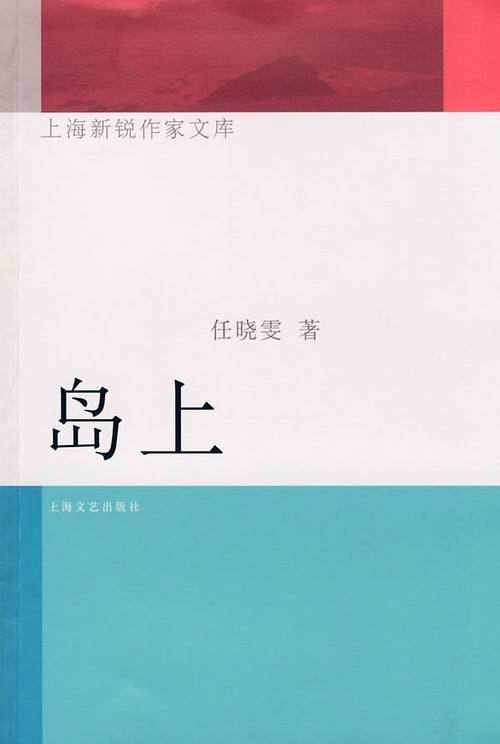

“在我看来,文学就是那条河:不同时段天气,呈现不同面貌;在这变化之下,却又隐含不变,使得时光更替,岁月流转,都不至于无序和幻灭。文学精神,就是这静止恒定之物。”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作家任晓雯对于文学的理解几乎是一段诚挚、长情的告白。无论外在如何变化,她始终恪守着这份感情,然后化作文字一点点流淌出来。
然而她又是无法被标签所固定的,“美女作家”、“才女作家”等称谓只能让她感到尴尬,她只是凭着个人兴趣和关注重心的转移,从小我写到他人,从现实当下写到历史深处。《岛上》虚构了一座充满人性恶的小岛,《她们》勾勒出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的一批女性群像,《生活,如此而已》展现一个年轻女子前半生的精神困顿,仍在延续中的《浮生》系列则工笔细描了一个个血肉丰满的小人物……她无意依靠一部作品留世:“我不是‘一部书作家’,我以后的人生里,也许有几十年要以写作为生,我没有兴趣把自己有限的阅历拿来一遍遍书写。世界那么大,时间那么绵延无尽。掌握处理资料的能力,能够给我的写作以极大自由。”
每周写作六天,每天写作三个半小时,为了避免被各种社交网络诱惑,写作时把手机放到很难够到的橱顶——在写作这件事上,任晓雯态度认真得像个学生。她对于文字的态度也认真得近乎苛刻。近几年的写作中,除了陆续见诸报章,收获了赞誉的《浮生》以外,她一直在写一部横跨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穷尽一个女人毕生悲喜荣辱的小说。2015年,在改了三稿以后,小说中部分片段以《药水弄往事》为名发表在《花城》杂志,随即入选《2015年中篇小说选萃》等选集,并获得了当年《中篇小说选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但她并不满足,因为“文字没能让我自己满意”,于是再改——前后总共写了五稿之后,这部名为《好人宋没用》的长篇小说终于尘埃落定,近期由《十月》杂志推出。
“我要写一部个人心灵的历史,在这里,国家和时代只是这个小人物的背景色。”
记者:作品虽名为《好人宋没用》,但“好人”并非寻常意义上贡献于他人的好,名字的“没用”也并非一无是处,这两种看似有些矛盾的设定却恰恰是主角宋没用身上最突出的特征,可否解读一下这个人物?
任晓雯:《圣经》里说:“没有好人,连一个也没有。”倘若要我塑造一个全然高洁的人物,我想我是塑造不出来的,因为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宋没用当然不算道德楷模,她身上有懦弱、自私、狡黠、随波逐流的地方,在人生最重大的事情上也并非完全明白。但她心地柔软,常有怜悯,这让她在黑暗之中,依然存留人性的光芒。
回想中国现当代长篇,几乎没有以小人物命名一部几十万字长篇的。有《张居正》,有《李自成》,但是他们已是留名于历史的大人物,文学书写似乎只是锦上添花。
记者:所以你希望关注的是那些被时间掩埋、被历史遗忘的小人物。
任晓雯:我的确很想探寻一下,普通中国人是怎样的,他们如何回应苦难,如何看待死亡,他们灵魂深处有什么秘密。所以我要写一部个人心灵的历史,在这里,国家和时代只是这个小人物的背景色。
宋没用就是这么个小人物,被历史遗忘了名字,被时代筛漏了生命。父母称她“没用”,子女也认定她“没用”。她属于刻板印象中的中国传统妇女。这个群体让人联想勤劳、善良、任劳任怨等词汇,这些词汇却也使得她们形象浑浊。她们是生活的配角,往往也是文学的配角。现当代中文作品中闪闪发光的女性,多是鲜活多汁、泼辣生风、敢于冒犯禁忌的。而我想写的“中国传统妇女”,并非所谓典型形象,而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多年来,一位老太太在我脑海中婆娑走动,挥之不散。那是我的奶奶,浙江象山人,执拗、敏感、心地柔软。除此,我对她的个人际遇,几乎一无所知。那时我太年轻,没能怀着体恤之心去爱她。我虚构了宋没用,部分出于对她的缅怀。
记者:小说用了很长篇幅描摹宋没用的一生,可以说,她的一生既未经历高峰,也不曾彻底坠入深渊,只是在时光流逝里慢慢生长,被时代洪流席卷着身不由己地漂泊,又一点点耗尽了所有的精力和生命力。她既是一个人,又像是很多人——很多在历史中被遮蔽、被淹没的个体。在选择这样一个书写对象时,基于的是什么考虑?
任晓雯:宋没用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太太,似乎谁家都有一个,耳聋、多话、皱皱巴巴。她是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浮生》系列里的人物。两千字意犹未尽,便写成了长篇。我以前写过激烈的故事,以后也还会继续写激烈的故事,但这次就想写个最普通的小人物,其实这很难写。我很喜欢福楼拜的一个中篇,叫《淳朴的心》。我每年都重读,每次都被小说中的文盲村妇费莉西泰打动。高尔基说:“为何我熟悉的简单的话,放到描写一个厨娘‘乏味’的一生的小说里去,就这样使我激动?这里隐藏着不可思议的魔术。”这是对小说家的至高赞美,也是《淳朴的心》反复激动我的原因。其中有技巧的力量,但不仅仅是。费莉西泰的故事,是一个用爱抵抗苦难的故事。直至很久以后,我才能真正读懂,为何福楼拜将这位普通农村老太太鸡零狗碎的一生,与圣徒(《朱利安传奇》)、圣人(《希罗底亚》)的经历并称为《三故事》。卡尔维诺认为,“《三故事》中的三则故事几乎是福楼拜所有作品的精华”,我是完全赞同的。在我看来,宋没用的人生还不够平淡,至少比费莉西泰曲折多了。我其实很想试试写一场完全没有波澜的人生,可惜在中国的每位老人,都经历过巨大变动。因为苦难太普遍,所以我们习以为常。如果愿意搬个小板凳,坐在老人面前,说:“奶奶,你经历过什么,告诉我好吗。”可能会收获非常精彩的故事。但是我没有机会这么做了。
“掌握处理资料的能力,能够给我的写作以极大自由。”
记者:在你近期的作品中,包括陆续刊发在报刊专栏上的《浮生》系列,以及《好人宋没用》,可以看出作家关注重心的改变:从当下回到过往,从现实场域回溯到上世纪整整百年里的各个历史场景。对你而言,并非直接接触的现实,而是需要大量采访、资料搜集和案头工作下才能形成的过往为什么那么吸引你?
任晓雯:《好人宋没用》和《浮生》系列其实都有历史,也都有当下现实。其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与现实同在的。也许因为历史细节与我们的经验有疏离感,所以才让人印象更深刻吧。写完这两本作品,我最大的感受是,我掌握了运用资料的方法,“写什么”不会再成为我的问题和障碍。我不是“一部书作家”,我以后的人生里,也许有几十年要以写作为生,我没有兴趣把自己有限的阅历拿来一遍遍书写。世界那么大,时间那么绵延无尽。掌握处理资料的能力,能够给我的写作以极大自由。
记者: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上世纪70年代生的作家多多少少曾受国外译作的影响,不少作家据此形成的写作风格一直沿袭至今。在你的写作中,却可以看到近年来在书写风格、表达方式上逐渐“去西化”,为何会做出这样的改变?
任晓雯:我也受了国外译作的影响。对于西方文学的阅读,形成了我小说写作的底色。语言的变化是一步步的。我先把繁复的欧式长句消化干净,然后融入文言,最后再是沪语。目的是想让语言和人物及氛围融为一体。我写的人物多是上海小市民,用“英译中”的叙述腔调难免有点隔。所以力图简洁,准确,中国化。但是这还不够。在叙述历史故事时,我把语言做旧,以此制造年代疏离感。就像用老镜头拍老电影,让镜头蒙一层淡淡的昏黄。其实《好人宋没用》前后的语言有细微差异。开篇是1920年,因为年代久远,所以语言更紧凑些,富含古典意味的字词用得更多,虚词用得更少,年份也以天干地支为计,比如“丁卯年”这样。从50年代以降,中国人的生活境遇与语言习惯变化非常快。我从1920年写到1995年宋没用过世。如果描述90年代时,语言还是如此古朴,未免有些做作。所以我随着书写年代的推移,渐渐减少古语字词,同时增加虚词以舒缓语速,并且在1949年以后,改为以公元计年。
记者:所以在《好人宋没用》的语言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短句、白描、口语化叙述都是经过反复磨砺才呈现出来的。
任晓雯:对,在上述语言习惯随着年代变化的基础上,有一些从明清小说里习得的字词用法,我保留了下来,尤其是动词的用法。名词决定了描述的丰富,动词则决定了生动。古典语言里的动词,往往有以一当十的风采,这是翻译体所欠缺的。比如《水浒传》中,好汉让店小二多拿些吃的,店小二便“铺”下一盘牛肉来。简单一个“铺”字,让人即刻想象画面:盘子大得豪放,几欲盖住桌面,牛肉在上头满当当摆开着。
而沪语的融入,也是为了让我的笔下人物更生动。我从来有个习惯:只有看到人物在头脑里走动起来了,才敢动笔。当我把上海话放进来,头脑里的人物突然有了不一样的鲜活度。我甚至能感受到他们噼里啪啦说话时,带有口腔气息的唾沫向我溅射而来。《好人宋没用》里,最早的方言不是沪语,而是苏北话,比如“小把戏”这种称呼,就是来自苏北。沪语里面很多都是外来语,融合了英语、浙江话(主要是绍兴、宁波话)和江苏部分方言(苏州、扬州话等)。宋没用从阜宁到上海,正是苏浙人大量移民上海的年代,里面的绝大多数人物都是外地人。所以在《好人宋没用》最早的章节里,各种方言和洋泾浜英语都有。写到晚近年代,才是我们当下日常的上海话。
“写作是艰难的。我满怀问题意识,却又必须将人物还原为人物,把文字放手给文字。”
记者:对于写作者而言,生存与死亡永远是最终极的书写题材。因为横跨70余年的时间长度,《好人宋没用》中写到了许多人的死亡,有的缓慢痛苦,毫无尊严;有的突如其来,猝不及防。而生存,则像宋没用说的:“活着这件事,好比饭菜端到面前。再难下咽,都得吃光。”你如何看待写作中的生存与死亡命题?
任晓雯:死亡是苦难中的苦难,是人类面临的最重大、最绝对,也最具普遍意义的苦难。某种程度而言,关于饥饿、穷困、战争、离乱的描述,只是书写死亡的无数种变体。
叔本华有一句被鸡汤化了的话:“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当我们在这可见的物质世界中,被内心欲望推动着跌来撞去时,所欲所求的任何一件事物,都不能给我们带来终极意义。得不到,痛苦。得到,无聊。“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无法从“活着”本身推导出来。
必须思考死亡。如果人类永远不死,活着这件事情就丧失了意义。时间的流逝就丧失意义,成长的喜悦、衰老的忧伤、劳作的辛苦、暂时的得到与失去,对生活可能性的期盼与失望,全都丧失意义。不死的肉体,只配拥有懈怠和疲惫。难怪托尔金认为,死亡是造物主最好的礼物之一,因为人类天生的本质无法承受不朽,“延长存活时间就像将一段金属丝不断拉长,或把黄油越抹越薄,这会变成无法忍受的折磨”。
一个人怎样信仰,便怎样生活。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了对生存的态度。有人生得糊涂,死得混沌。有人不相信死后审判,便决定在有生之年,向这个世界无限索求。而信奉“人死如灯灭”的,难免陷入“活着没意思”的虚无,因为他们的生命,看似是被随意抛到世上,白白承担劳苦愁烦,然后无意义地消逝掉的。
在思考死亡之后,关于生命的形而上辨析才能展开。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绝望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绝望,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相比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更认同的是“未知死,焉知生”。
这是我对死亡的看法,也是宋没用对死亡问题的摸索路径。她生命中有四个重要人物:没有名字的母亲、婆婆杨赵氏、东家倪路得、女儿杨爱华。这四位女性的内心风景,部分构成了中国人在信仰和死亡问题上的精神光谱。而宋没用自己呢,在我看来,她是仰望者、探寻者,是旷野中的飘荡者。
我用“在我看来”这样的措辞,是因为宋没用是我,又不是我;是每一个人,却又是“这一个”。宋没用不是观念的传声筒,她拥有自己的体验、智识,和自由选择的能力。所以写作是艰难的。我满怀问题意识,却又必须将人物还原为人物,把文字放手给文字。像尊重一个真正的生命那样,尊重笔下的人物。像重视一切工作本身的逻辑那样,重视文学的逻辑。关于写作和生命的思考,不过是一根提引着我的隐形之线,让我不至于迷失在中途。
记者:除了表达方式和书写语言的节制以外,阅读中,常能感受到写作者在情感上的克制,比如书写苦难。穿越动荡岁月的人难免历经苦难,作品中每个人都曾亲历苦难,至少也见证了他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但在书写上却极少对于这种情绪加以铺张,反而隐而不发,从细微处见波澜。
任晓雯:我认为高级的艺术都是节制的。好比优秀的演员,一个眼神或者动作,就能把角色的痛苦欢乐表达出来。那种永远在大哭大笑大叫大闹的演员,是令人生厌的。
记者:此外,不少青年作家会选择自己最擅长和熟悉的领域进行创作,这使得他们的作品有较高的辨识度和比较固定的读者群落,而在你的创作路径中,却拥有一条持续生长的轨迹,很少在某个阶段停留。你似乎并未定性,也不愿意给自己定性,而是努力探索着写作上更多的可能性。
任晓雯:我对自己的写作有两点要求:坚持写,永远不满意。我没有刻意改变风格,只是每写一本,都对自己提出更多要求,作品就不知不觉有了变化。我作为青年作家写到了中年作家,以后还要再写成老年作家,老是一个调调多无聊啊。如果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在不停重复,那我就不写了,因为我的想象力和写作事实上已经死了。
记者:相对于以前的书写而言,《好人宋没用》在情节推进上更为缓慢、叙述绵密,是在书写难度上对自己的一次挑战,这样的写作必定是漫长而耗费心力的。
任晓雯:一天一天写,每天把规定的时间写足。想想自己正做着喜欢并且擅长的工作,不用熬夜,不用风里来雨里去,不用搞复杂的人际关系,于是就很快乐,完全感觉不到什么“漫长”、“耗费心力”、“挑战”之类。所有工作都是不容易的,要感恩,要知足。
记者:在完成这部长篇小说之后,近期是否有其他创作计划?
任晓雯:今年《好人宋没用》和《浮生》系列都要出版了。目前在写一本短篇小说集,已经完成半本,写完短篇集再会写个短点的长篇。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