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需要充当一座桥梁,沟通东西部,沟通历史与当下,沟通当下与未来。我的坐标就是:横的时代,纵的历史。这部书就是在这样一个坐标系上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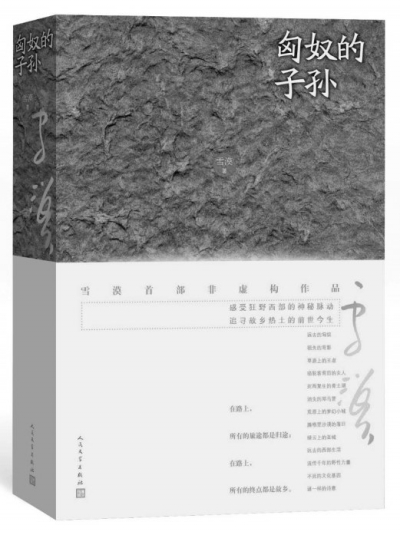
《匈奴的子孙》,雪漠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雪漠完成了心中的一个梦想。他走了很长的路,横跨了半个中国,见证了这个时代的中国,也见证了故乡在二十年后的改变。这些变化之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不那么让他欢喜的一面,但他知道,每一面,都是时代的必然。
一切都在变。对人来说,选择向上的变化,拒绝向下,需要文化的力量。雪漠的《匈奴的子孙》,虽然是对一场文化考察的定格,但又何尝不是对这个时代的中国的一种定格呢?如雪漠所说,真正的有心人,或许会从中汲取自己需要的营养,扬长补短,像麦积山石窟的工匠们打造艺术圣城一样,打造自己的灵魂和人生。因为,这里毕竟隐藏了那么多的命运轨迹。
中华读书报:请您说一下这本书的缘起好吗?
雪漠: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自己开车或乘车,找一些我最感兴趣的地方走走。当时,从岭南开车去西部没有想到要写书,只想完成生命中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带着家人和几个朋友,一起去经历一个个地方,记录下我们的感受,记录下各地的人文,和可能很快消失的一些画面。
从岭南出发,一路穿越半个中国大地,最后到达西部凉州。然后又到藏地进行考察,考察了卓尼、临夏等很多地方,甚至深入乡村,走了一个个的村庄。这种生命的体验凝聚在三本书中:《从岭南到西部》《山神的箭堆》和《匈奴的子孙》。时光在消失,生命在消失,文化在消失,生活在消失,一切都在消失,书中记录的这些东西,可能一些人现在感受不到它的珍贵,但是五十年之后,这些东西都会消失,其实要不了五十年,现在很多东西都已经消失了。
中华读书报:您觉得自己的作品和其它同类探险或考察的图书相比有何区别?
雪漠:当我们看探险家斯坦因写的明末清初的那些游记、探险记、考察记的时候,会非常感恩他们保留了那些非常宝贵的资料。我是以作家的视角,更侧重人文,侧重生命本身,侧重每一块土地。它们会带来不可替代的感受。有人问,这些东西消失之后,保留它们有什么意义?我说,消失的只是现象,保留的是一种精神,它是根。我们的生活像一棵棵大树,而我们的文化是根。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深扎在不同的大地。
《匈奴的子孙》是心灵自由飞翔之后的产物,希望能够给朋友们带来一种启迪。作家需要充当一座桥梁,沟通东西部,沟通历史与当下,沟通当下与未来。我的坐标就是:横的时代,纵的历史。这部书就是在这样一个坐标系上完成的。
中华读书报:在这部书里,上篇是大地的记忆,追溯历史,通过对《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等史料的研究,把西部的根推到秦汉以前了。在下篇里又有当下的脚步,对现在的西部是什么样子的,又有一个实地的考察,历史和当下形成了一种呼应,也就是远古和现代又形成了回应。对于西部文化,在这部书里,您有一种追问,想要寻找西部文化的根。那么,您觉得文化在它的历史发展当中,如何保持它的独特性?
雪漠:世界的独特性终将消失,这是一个趋势。未来甚至现在,每一个城市都差不多,每一个地方的商品也都差不多。所以,除非有一批有识之士,有意地抢救、保留一种文化,否则这种文化的消亡是必然的。
独特性其实就是地域文化对某个群体打下的一种印迹。印迹很重要,但终将会被淘汰,就像匈奴终究从我们的世界中消失、大月氏从我们的世界中消失一样。这种消失是一种必然。但是,在这种淘汰之中,我们需要能保留一种精神,要有保留精神的独特性。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怎样才能坚持精神的独特性?
雪漠:一是文化传承。文化的传承就是一种独特性,文化同样需要信仰,让你能够为之坚守和拒绝一些东西;二是需要一些专业人士,需要有眼光的有识之士,还需要借助民间的力量,大家一起挖掘身边的文化的独特性;第三,还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非常重要的;第四,需要各级政府关照,否则,民间文化也会慢慢地消失。
一个果子成熟后必然会腐烂,需要一些园丁不停地将这些果子播种下去,一代一代长出新的果树,跟其它优秀的果树进行嫁接,出现新的品种。文化也是这样,它需要多种嫁接,需要土壤,需要一批又一批的园丁,没有这些努力,很多文化就会消失。
中华读书报:您一直用自己的方式不断地去和时间抗争。您的写作有一种悲情英雄的姿态,总试图定格即将消失的文化,让它能够留在作品中,或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关于西部,您写了那么多的书,《匈奴的子孙》在您的生命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雪漠:《匈奴的子孙》在我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在我生命的黄金时代,放下一切去品尝的人生经历,是根本抹不去的。
我的每部作品,都不是可有可无,都是我的经历,是构成我生命的一个个零件。我为自己的生命设置一种新的可能性,追求一种自己不曾追求的经历,跟世界发生的关系,跟自然发生的关系,跟群体发生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人生的丰富性。你对社会的贡献,又构成了价值。《匈奴的子孙》就是这一理念的产物。我总想突破自己,换一种写法,为世界提供另一种精彩。
中华读书报:匈奴文化代表的游牧民族和野性基因是如何在西部大地上流传的?今天的西部还能不能找到它们的影子?
雪漠:其实,西部文化中的很多文化就是匈奴文化和中原文化,以及多民族文化杂交的结果。目前,你如果具体地说西部文化中哪个文化是匈奴文化,已经很难了,但是里面诸多的文化中仍然带有匈奴的影子。比如,早期的匈奴是萨满教,现在的西部文化中“万物有灵”的观念仍然存在,仍然留存于凉州文化中。其实,凉州文化也影响了中国的大一统文化,比如佛教,比如中国的建筑,都受到凉州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其发祥地就在凉州。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论稿》里,就有许多相应的证据。
中华读书报:“故乡三部曲”和《匈奴的子孙》都是扎根于西部的作品,一些读者因为读了您的书,才对西部大地产生了浪漫而真实的向往。西部真的那么美吗?关于西部的真实和浪漫,您最想对读者说什么呢?
雪漠:当然,西部不仅仅是凉州,还有敦煌、甘南、西藏、新疆等。西部确实很美,它不仅有大漠、雪山,还有草原,更有独特的民俗文化和民情风俗。我们不要说拉萨、敦煌,就像甘南草原、拉卜楞文化,以及新疆等地的文化,都有神秘而吸引人的东西。直到今天,我对西部仍然很向往,并且每年都要回去住上一段时间。
其实,西部有点像蜂窝煤,一个文化圈又一个文化圈,环环相扣,构成了十分复杂的迷宫一样的格局。它们相互独立,各呈异彩,绝不雷同。西部文化既是一种杂交文化,更是一种本有的独特文化,很难为其他文化所影响。它既有封闭性,又有很强的包容性。封闭性就是每种文化都有一种历时千年的特点和传承,不为外界所熟知;包容性就是它可以包容外来文化,但是外来文化进入这个文化圈之后,有可能会出现变异。
中华读书报:“西部”已不再是地域概念,更是文化概念,也是一种符号。中国的“西部”如何将地理概念变为文化概念?
雪漠:中国的西部对中国文化总有一种强有力的影响。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说,在每个历史时期,每当中原文化显得非常疲软的时候,少数民族文化总会强有力地进入中原,为中原文化激起一股新的活力。在中国文明史上,这种现象已经非常多了,如大唐,如满清,如元朝,都有一种少数民族文化的介入,而使整个民族文化呈现出一种强悍的倾向。
西部文化在中国版图上更多的不是一种地域性的东西,而是一种介入性的文化。这种介入的力量非常强悍,因为西部有种强悍的基因。很多时候,少数民族文化——比如匈奴文化——总是以一种强有力的、不可抵挡性的特点进入中原,直接影响并改变着中原文化。所以,它的这种干预性、介入性,有点像野生水稻和传统水稻的基因嫁接,嫁接之后就会产生出新的品种。中国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变化,都是少数民族文化介入的结果。直到今天,西部文化仍然是这样的,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挖掘和研究。
中华读书报:您说《匈奴的子孙》是心灵放飞的产物,在创作中是否完全达到了自如的状态,这是一种怎样的写作呢?
雪漠:现在,我的创作已经是生命的本能了,它就像灵魂在跳舞,完全没有了创作的概念,也远离了一些所谓的技巧,更不会考虑文学的一些理念,它是一种自由性的东西。目前,我只想保留这块土地马上就要消失的东西,定格一种存在,为历史展示一个作家独有的角度和方向。其实,书中写的很多东西,现在看来司空见惯,但是几十年之后,这一切都会成为历史的定格,成为历史的绝响。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