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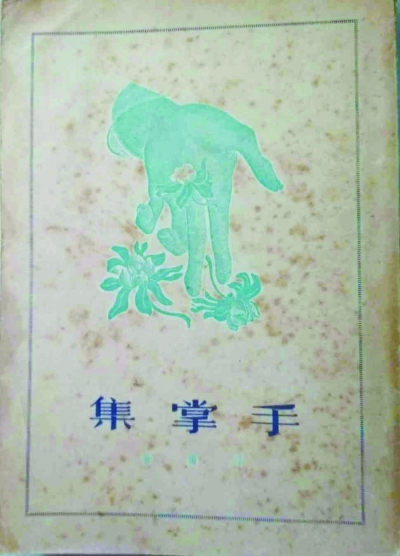
诗人辛笛的代表作
吴霖
20年前我曾写过辛笛访问记,文章第一句这样写:“和辛笛先生握手!他的手掌,凉凉地。”
访问辛笛的那一次,他送了我一本诗集,是1986年版的《印象·花束》,签了名、盖了章。现在舍下的一本1948年版的《手掌集》应该是后得的,不然,当时也一定会请他签名留念。
辛笛说自己写得最好的诗,在《手掌集》中。《手掌集》是辛笛的代表作,也得到诗歌史的公认。这本《手掌集》,1948年1月由星群出版社出版。印数1050册,其中用西报纸印了1000册,道林纸本50册。是年8月,该书再版。出版者改为森林出版社。内容没变,与星群版不同处,一是封面做了改动,原由辛笛亲书的“手掌集”和“辛笛”五字,改成了美术体。二是在版权页上,增加了发行人辛白宇。就如同印刷者是子虚乌有的森林印刷厂一样,至今仍未有人揭秘这个在一批以森林出版社出版物上赫然在目的发行人是为何人。是曹辛之?是辛笛?抑或谁都不是,只是障眼法而已。再版印数不载,想来不会多过初版的数量。如今,初版、再版均不易寻见。品相上佳的,更珍稀如凤毛矣。
诗集由辛笛本人在1947年底编成,根据创作年代分“珠贝篇”、“异域篇”和“手掌篇”三辑。每一段的引首,都有一小节英文诗歌,分别来自霍普金斯、艾略特和奥登。所引诗歌,想来都是作者所喜爱的。这是一个汉语诗人用诗人的方式在向英语诗界的前辈作遥远的致敬。
1948年的元月,辛笛随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前往美国考察,随身只带了一本《手掌集》样书。在旧金山,辛笛喜遇清华时代的同窗好友唐宝心,遂将这身边仅有的一册诗集题词赠予。唐宝心归国时,携回此书。在后来的生活跌宕中,所有书籍被无奈散尽,此书自未例外。在流浪了若干年后,这本《手掌集》被爱书人姜德明(著名新文学版本藏书家)慧眼收藏。他在以后终于云淡风轻的日子里,分别找到了作者和受赠人。于是,这一本曾经珍重相赠、认真庋藏、又流离冷摊的诗集,有了“回家”的幸运。
1931年辛笛从天津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未几,负笈英伦,回国后进入上海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是辛笛的父执和同乡。在海外和回国之后,他一直没有放弃诗歌。直到他与星群出版社的诗友们猝然相遇。
最初成立的星群出版公司(星群出版社)酝酿于重庆,由同道朋友集资所办。参加的人有曹辛之、郝天航、林宏、解子玉,臧克家未出股金,但以《罪恶的黑手》和《泥土的歌》两本诗集的版权作为投入。故此,此5人应该是星群出版社的原始出资人。到了《诗创造》创刊,在曹辛之的叙述中,增加了沈明,减少了解子玉。前期的《诗创造》没有名义上的主编,诗稿由大家分看,曹辛之负责编务,最后汇总征询一下臧克家的意见。虽然可能他们都视臧克家为精神上的“带路的人”,但也为后来该诗刊在编辑方向走向上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星群出版社出版的书和《诗创造》得到了读者的拥护,但由于出版印刷和销售回笼资金之间有较大的时间差,加上物价飞涨,出版社很快就捉襟见肘。这时,臧克家介绍曹辛之认识了辛笛。曹辛之晚年称:当时出版社“经济压力很大,主要经济来源靠向辛笛同志所服务的银行借支。辛笛在这方面帮了大忙,如没有他的支援,出版社早就停业了。”
出生同一母体——星群出版社(森林出版社)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或许在政治(反蒋和亲近共产党)上并无太大的分歧,促使他们分野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在诗歌创作观上的迥异。刘岚山在1948年6月对臧克家的访问记中,写到臧的诗歌观:“他觉得现在的诗,应该朴素有力,适宜于朗诵,而富于人民精神。对于空喊‘艺术性,永久性’以掩护自我中心的落后意识与情感的诗作品,则猛烈抨击。”刘岚山本人也是诗人,他认为,《中国新诗》“这本诗刊从发刊词到作品,都比较隐晦,显然有现代派意味……”有着现实主义诗歌观的他,当年曾用化名著文批评《中国新诗》。他感到内疚的,是从未向好友曹辛之坦诚说明此事。
《中国新诗》的提议者为辛笛,经费问题也由辛笛所工作的金城银行贷款解决。子虚乌有的森林出版社因为没有实际地址,最后请在邮局工作的唐弢申请了一个邮箱代替。但发行者仍为星群出版社。《中国新诗》每月一期,一共出了五期,便和星群出版社和《诗创造》一起被当局查封了。
1948年底,星群出版社被查封时,臧克家一度东躲西藏,也曾以“北方朋友”匿名被辛笛带回中南新邨的家中躲避数日,还曾躲到李健吾家中,后来实在无法,找到党组织的联系人陈白尘(之前的联系人先后为以群、蒋天佐,此时均已去了香港),陈写了条子,让臧去某银行找某人可取700元“金圆券”,以为路费,嘱可去香港找以群。辛笛知道臧克家要逃难远避,再一次伸以援手,慷慨赠予2000元。虽然当年金圆券的实际价值俟考,但700和2000的对比,也可以确信辛笛此举,无疑于“万人丛中一握手”,臧克家由此感念了很多年。
黄裳为南开中学的同学好友黄宗江编了一本散文集,但出书却很不容易。某日跟辛笛说了后,此书很快就印出了。这就是1948年12月森林出版社出版的《卖艺人家》。封面题签黄裳,装帧设计曹辛之。道林纸印、毛边。发行人,照样是面貌不详的辛白宇。扉页上,印着黄宗江的题词:“纪念亡友郭元同——艺名艺方”。这位郭元同,是黄宗江在燕京大学的同学,也是他妹妹黄宗英第一次婚姻的对象。这一册小书,给朋友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作者而言,“垂老难忘”(黄宗江语)是可以理解的。但很多年后,老资格的出版家范用还建议,称这个版本应该原封不动地再印一次。可见此版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深。
辛笛在中南新邨的住所,曾给诸多文化人留下深刻印象。施蛰存的记忆里,辛笛家的栗子粉蛋糕极好、极好。黄裳的评价是:辛笛是好客的,文绮夫人烧得一手好咖啡。钱钟书的“雪压吴淞忆举杯”诗中,记录了第一次登门,和徐森玉(辛笛岳丈)、李玄伯、郑西谛、陈麟瑞(柳亚子女婿)等人一起享用火锅的旧事。
解放之初,此处房子卖出,辛笛一家搬进南京西路曹禺原来租住的房子。和辛笛在“更正朔”之后,与文学界虽然且行且珍惜,但在离开银行界后却一踅走进工业界直至退休一样,辛笛当年的选择,回头看,属明智之举。
在李健吾的文字回忆中,曾写过“辛笛家的扬州菜,特别是扬州汤包,到现在想起来,舌根还有留香之味。”当年,辛笛有自备车代步,家里还请有一位淮扬菜厨师。以淮安为代表的淮菜跟以扬州为标志的扬菜固然同属一类,但细究起来,还是小有差异的。辛笛原籍淮安,虽然自小长在天津,但口味还是最乡愁的。当年他家那一位大师傅推测应是烹淮菜小鲜的好手。告别中南新邨后,这位淮扬厨师也就散去,惜乎背影隐然,不传其名。另,辛笛飨客,每以佳肴待之。其本人未必是老饕,但应是行家,惜乎在他留下的文字中,关于美食,终于不著一文。
辛笛是典型的读书人,但待人处事有豪迈之气。鼎革之年的7月,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辛笛请一批文化人吃饭,吃得高兴,于是第二天又请了一次。方令孺称辛笛是“慷慨好客”的“小孟尝”。1983年新疆举办诗会,当得知有的青年诗人因路费无着时,他又解囊相助,不计回报。
黄宗江在辛笛去世后曾著文回忆,文字还是一如既往地旁逸斜出。其中精彩的一节,直可入当代《世说》:
我来沪,黄裳兴高采烈地说:“辛笛又可以请客了”。当然要请!辛笛问我去哪儿?我说上海有一家可吃东坡肉比杭州的不差。结果却是食兴大败,只因那时百废待兴,又百业难兴。扫兴之余,辛笛击案曰:“重请!”
1997年岁末,我登门拜访辛笛先生。他的家,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西路上。房子是老式的,略有些美人迟暮的味道,但立面挺括、建筑细部一丝不苟,终使这所老房子保有着自尊和雅的品位。我和辛笛先生相对而坐,当我说出对这房子喟叹时,坐在远处沙发上的辛笛夫人徐文绮清晰地告诉我:房子是维多利亚式的。
那一次,我曾认真地请教辛笛:诗歌还有希望否?刚刚过了87岁生日的辛笛老人,行动不便、嗓音嘶哑的他,很果断、很坚定地一挥手说:新诗肯定有希望!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