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宇澄近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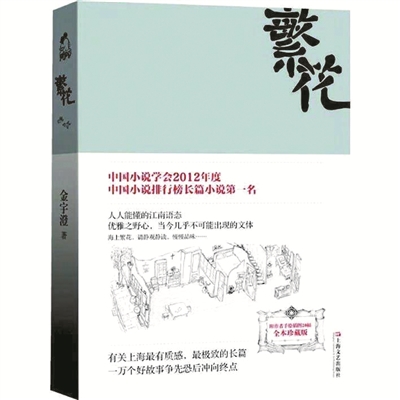
《繁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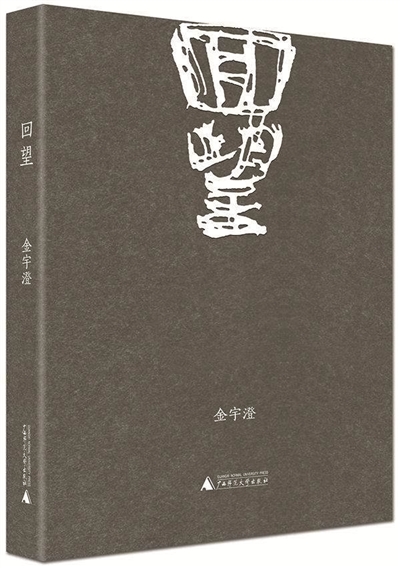
《回望》
因为小说《繁花》摘得茅盾文学奖,作家金宇澄声名鹊起。多次在上海书展这样的城中文化活动中见到金老师。他衣着极为随意、根本没有发型,忙得出席完一场活动,名字又出现在下一场活动的嘉宾名单上。长篇小说《繁花》之后,2017年金宇澄又出新作《回望》。金的父亲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时期中共情报人员。他在这部作品中以非虚构的方式书写父母的往事,尝试着探寻一些父辈“烂在肚子里”的秘密往事。作品一问世再次受到文学界的关注。
近日来,他正忙着和墨镜导演王家卫把《繁花》拍成电影,这个编剧和导演的搭档卡司,让人对这部电影油生想像,也能明白他有多少细碎工作要做。但百忙之中,金老师还是接受了记者的访问。为节省时间,他最后选择了电邮采访的方式。看到他深夜发回的邮件,记者庆幸这个采访方式的选择——因为他的个人思考没有被再度“翻译”,你能在这些答复文字中感受到一个作家的追求、警醒、温度和诚意。
关于《繁花》和《回望》
问:《繁花》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浓郁的上海味道,但它又不是纯粹的方言小说,北方读者也完全能读懂领会。这种能令读者感受到明显地域特点的写作是您有意追求的吗?如果不考虑兼顾读者群,您是否认为一本沪语《繁花》会更纯粹、更有精髓?
金:小说的语言很重要,读者第一时间看的就是语言,我们已经习惯了用普通话或者北方方言的写作,吴方言是另一个系统,难以驾驭,但它是自然的生成,生动而活泼,如果只原汁原味照搬,会失去创作的特质,必须经过选择和改良,才能产生更丰富的文学魅力,是更纯粹的写作精髓。
问:《繁花》写的是普通人的琐碎日常,但它每一章节又在前后时代中跳跃。全书文字非常考究、技法又很灵活,有读者说它是考验读者是否懂文学的标准和尺度,对此您怎么看?
金:时间已经流走了,听一首过去的歌,提一个过去的故事,复杂的感怀,每位年长者的回忆,青春的时代,有没有意义?《繁花》等于看一盘过去的录像,我完全忘记了这些事,完全忘了,意思就是这盘带子对记忆是无意义的,但是我一看,曾经的那些人和印象就开始复活了,让我极为惊讶,不是幸福,也不是痛苦,这种重现,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感受。我关心城市生活,关心普通人的立场,希望他们可以自由说话,包括密集的章节、简单的标点、旧文学元素等等,喜欢写作意义的挑战,写作和阅读,一直需要这样的实验精神,我也知道如今我面对的早不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读者了,而是更挑剔、更见多识广的读者群,在这严峻的环境下,只有写出我最喜爱最熟悉的内容,提供最特别的样式,从内到外都得这样认识,才是一种挑战。
问:您书中对女性的描写细腻入微,令人印象尤为深刻。多次在书展等场合看到您,您不太细腻的形象和极端细腻的文笔有很大反差,非常好奇这两者是怎么统一的?您对女性的细微体察是怎么得到的?
金:老舍先生讲的“上知绸缎,下知葱蒜”,现实主义的小说需要这样的体察,因为生活太丰富,你所遇到的人太丰富,读者对作者的要求也这样。必须仔细地表现人生的丰富性。
问:我仔细看了您的新作《回望》。您用三种不同的叙事对自己父母的一生进行了梳理定格。他们的过往生活,鲜明生动,比如地下党员父亲被捕的细节、他在新形势中对自我思想的剖析、母亲记述单位饭菜的品种价格、怎样涨了一级工资平衡家里的收支等等。但这种细碎的诉说并不令读者感到冗长,反而令人感到生活的质感、温度和真切的现场感。请问,您对写作语言有怎样的自我要求?是否一直在坚持树立一种自己的风格?
金:非虚构的写作,细节甚至决定了成败,如何处理材料,凸显细节,如何记录人的历史,都在于这些细节的动力,首先正也是这些细节打动了我,让我感知它的价值,值得去写,克制自己,不解释议论,只让细节说话,让细节组成曾经的图像,形成氛围,是我对这个过程的主张,如果没这些原材料的诱发,完成这本书是很难想象的。
问:《回望》的编排极其细致复杂,不仅书页间穿插的老照片清楚标明拍照时间地点背景,一些书信、明信片、剧本草稿、学籍证明、手写公函等影印件点缀其中,时代感扑面而来。请问,这本书的设计思路是怎样的?您是怎样把握从庞杂的家族史料中遴选材料的标准?
金:家里确实保存了不少的材料,父亲过世后,有一天母亲拿出一叠信件说,你爸爸写的信,根本不知道他的这些内容……这是父亲和老友马希仁的通信,青年时代,他们就是朋友,但双方从不谈自己的事,直到了老年,才开始频繁通信,他们回顾年轻时代的经历,那时代早已过去了,到老年才可以谈,仍然历历在目,细节独到,身临其境,极为鲜明的现场感,那么具体,这束信件是写作本书的主干,引导我慢慢寻找关于它一连串的回答,寻找过去的声音和画面。历史最容易遗失的就是脆弱的细节,它们非常醒目,也非常容易散失,这个过程里有无数次梳理与选择,有挑战意义,却并不困难。
用编辑的眼光写小说
问:您曾说过,自己是用编辑眼光写小说的。什么是编辑眼光?它和普通写作者眼光有什么不同?
答:作为一位作者,看得最多的应该是文学经典,而编辑看最多的应该是来稿;作者一般不会清楚目前的写作基本面,编辑,则始终在这大宗的稿件里,寻找最特殊的文本、最好看的语言——这就是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
作者常常是自重、自我的,而编辑,永远是在冷静等待最为难得的文字与内容,永远在稿件之间反复地比较——甲稿和乙稿的差距是什么、这稿子的方式在如今是多见的,还是稀少的……这些客观的判断,作者不大会有。
问:当下,随着阅读形式的多样化,读者群细分化程度也非常高,作为一名纯文学创作者,您认为纯文学的前景光明吗?您觉得自己的目标读者是哪些人?
金:文学不会消亡,因为人与人永远需要对比和沟通,作为小说作者,我应该知晓眼前这越来越细化的世界,读者对文学的要求将越来越高,作者要打动他们,也将越来越难——我一直认为读者往往比作者更专业,我的写作目标,应该是有阅历、有文学见地、有幽默感的读者。
问:在《回望》的最后,您提到父亲在《日瓦戈医生》的封三白页上写道:“作家的任务是什么呢?知识分子绝不是沮丧和黑暗的。”您一直觉得这是他为您写的,那您现在觉得作家的任务什么呢?
金:留下这时代的质地,留下这个时代城市人的生活状态。
王家卫的《繁花》会是一部好看电影
问:有个大家比较认可的说法,好的小说很难改编成好的电影。作为编剧,您怎样最大限度地保存《繁花》的原貌呢?您认为改编过程中最不能流失掉的是什么?
金:改编《繁花》确实很难,尤其它容量的庞杂,以及王家卫导演独特的艺术方式,但一切还算顺利,保存上海的生活方式,保存时代质感,是原作的努力方向,也是导演的方向。
问:《繁花》里人物众多,沪生、阿宝、小毛、蓓蒂、银凤等等,这里面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主人公,他们在书中只负责讲述自己的生活日常。您怎么把他们揉捏到电影中呢?谁最应该承担主线的作用?故事的主线是什么呢?
金:即使小说的画面感再丰富,也只是文字的丰富,电影的途径不一样,是导演的艺术,它一旦走向银幕,体现的就应该是导演的全掌控,王导的许多方法非常有趣,我相信会是一部好看电影(我只能说这些)。
问:您觉得电影《繁花》应该是一部什么样气质的电影呢?它最好是静水深流的,还是缭绕更多烟火气些?
金:是一部体现了导演一贯的艺术方式的电影吧,他非常重视影片涉及的每一个方方面面。
问:每个《繁花》读者心中都会有一部自己的《繁花》电影,您觉得该如何区别欣赏小说和电影这两种形式?
金:看电影,也就是全面脱离书本的一种体验,文字的作用和声光电的效果,从来就那么不一样,因此以小说来判断电影,或以电影来定位小说,是过于简单的方法吧,除了欣赏,作为小说作者,我比较反对某种混合,即用影视剧的方法来写小说。谢谢。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