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羊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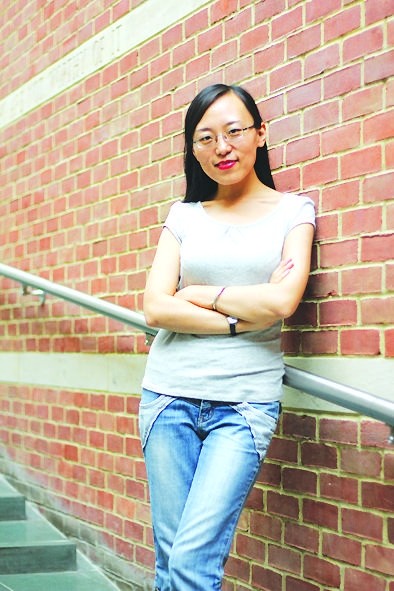
孙频

黄孝阳

曹寇

育邦

朱文颖

王一梅

戴来

韩青辰

李凤群
朱文颖:“新”意味着生命力、旺盛的创造力和探索精神
记者:作为一个20年前就已登上文坛的作家,此次作为“文学苏军新方阵”之一员亮相,有什么样的感慨?不妨从你作为一个作家的身份,还有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谈谈何谓“新”,如何“新”?
朱文颖:江苏此次推出的“文学苏军新方阵”都是由“70后”、“80后”作家组成,所以说,我即便在登上文坛的时间上比较早,但被归类于这个方阵的成员之一,仍然没有过于突兀的感觉。仍然是在代际上呈现着某种文脉的传承和延续的意味。而作为一个20年前就已经登上文坛的“老”作家,我早就习惯于被冠之以各种称谓,而与此同时清醒地知道“我是谁”。就像前几天我在北京参加首届“中欧国际文学节”,作为节目嘉宾参与中国全球新闻网的全英文访谈录制,我也并不会因此认为自己突然成为了一位“国际作家”……至于“新”这个字,我倒是颇为赞同、同时很想引用前一阵作家邵丽在描写几位“70后”作家时说的一段话:“将近20年过去了,她依然用最大的真实面对着文学、面对着世界也面对着自己。于是,在朱文颖身上,总焕发出某种新人的气场。这种新人之感,不是指向稚嫩,而是指向活力与不曾被磨损的生命力。”是的,“新”在汉语里的另一层意味,一直是生命力、旺盛的创造力和探索精神。
记者:你给我的印象是很江南的,而且是细小的江南,记得你写过一部名为《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的长篇小说。但你分明又是与江南保持距离的,从你的作品中,就像曾一果说的很难看到纯粹的江南气息。你笔下那个有意无意拉开一段距离的江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朱文颖:我刻意地、或者说有意无意与“江南”或者“南方”拉开一段距离,正是因为这两个概念都已经被泛化了,很难再从里面找到某种非常有力量的陌生感。而这种陌生感是一个作家终生在他的写作过程以及作品中追寻的。没有这种发现和创造,重复一个已经被固化的概念,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是失败的。是另一个指向上的重复写作。所以说,我不是不亲近“江南”或者“南方”,而是我要试图发现一个独特的、仅仅属于我的独一无二的南方。
王一梅:以轻写重,用简单的文字给孩子们讲述生命的话题
傅小平:以我的理解,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带有较强的设定性的,因为考虑到它的读者有很大部分是儿童,对他们要有正向的引导。所以,写给儿童的作品,一般都是积极的,即使里面的小主人公会经历一定的磨难,最后凸显的也会是人性的温暖底色。当然,写人性的温暖与明亮没问题,我想到的是,会不会影响作家对儿童更为真实的,更为带有纵深感的精神世界的开掘?
王一梅: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一直坚持热衷于温暖情感的描写,我甚至把反面角色也处理得不是那么“坏”,但我期待自己可以写写“坏人”,对比手法,是儿童文学写作的一个显著特征,假恶丑衬托了真善美,故事情节的展开也需要矛盾冲突。失败、死亡、失去、离别……这些话题,也同样是儿童文学常常描写的。我的长篇童话《雨街的猫》充满了等待的无奈和生命逝去的悲伤,我认为孩子可以读懂我童话中的情感世界,并且可以感受到伴随着无奈和生命逝去的是坚定的爱以及对生命的珍惜。
温暖而不失深度,悲伤却并不颓废,以轻写重,用简单的文字给孩子们讲述生命的话题,做起来并不容易,是我创作中追求的,也是我认为最为珍贵的。
记者:眼下儿童文学作家,会很自然地聚焦时代变迁如何改变中国式的童年的主题,所以他们的作品里,会经常写到留守儿童的生活,还有乡下孩子进城后的遭遇等等,让人读了深有感触,但因为题材的同质化,也难免会让人审美疲劳。因此,想问问你在创作题材的创新与扩展上有什么见解?
王一梅:我认为题材新固然重要,角度独特更加重要,同样题材如何写出新意,如何不露痕迹地写出深度,又如何敏感地捕捉到当代儿童生活的痛点、亮点和要点,不是人家写什么,我也写什么,这需要长期观察生活,长期阅读和写作实践,练就求异的思维,敏锐的眼睛。这点没有什么可以投机取巧的。我希望自己可以深入生活,深入了才可以发现,熟悉了才可以突破,我也希望自己可以把观察到的全部变成记忆,再抽离现实,去一个“真空”状态的环境中,提炼萃取新的物质。
戴来:小说的着力点是还原真相背后被遮蔽的那部分
记者:在我印象中,你的写作比较多地聚焦日常生活,就像刘艳说的,擅长透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折射出复杂的社会面,反映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精神难题。但我们眼下碰到的困境是,新闻、影像等等,已经过度侵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由此对于作家来说,怎样让写作从新闻资讯中突围抵达文学的层面,成了一个问题。换言之,这也是一个写作跟生活保持什么样距离的问题。
戴来:小说的叙述方式和新闻、影像是不同的,小说的着力点不是还原事实的真相,而是真相背后被遮蔽的那一部分东西,甚至我们对看到的真相是持有怀疑的。我们更关注的是呈现出的事实背后的心灵跋涉,新闻、影像可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触发点。
记者:我不确定是不是你把生活看得太透,在作品里索性把“我”也取消了。因为要把人世看透了,“我”没什么特别的,无非是小于或等于复数的“我们”而已。但凡事看透了,会容易滋生无意义感。写作除了求得实际的回报外,不就希望能找到那点所谓意义嘛。所以很多作家都会强调写作要解决精神疑难。
戴来:我倒没有觉得自己能看透世事,处理生活中的问题,我通常都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哪怕是复杂问题。这样处理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我在日常生活中是个无能的人。无能让我沮丧,同时也不得不坦然接受。
二十年过去了,没有改变的一点是,我依然觉得一个写作者所做的工作是呈现,呈现我们看到的事实和事实背后可能存在的更为复杂的真相,而非给出解决的方案或者做道德评判,至于寻找意义是评论家和读者的事。
韩青辰:对人物、故事血肉与共的培植过程是我给自己设置的难度
记者:不论把儿童文学界定为轻写作是否合宜,但我觉得它至少偏向于是一种轻写作。它让人读着轻松愉快,或是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情境里接受熏陶,学会思考,这一点在眼下手机、网络侵占阅读的大背景里,似乎更显重要了。这样的话,如果说你的写作是重的,那么在吸引儿童阅读上,你有怎样的考量?
韩青辰:我确实在思考怎么让作品更轻捷的问题。这种思考也是出于文学性和艺术自身的需求。写作多年,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不会写了。我在我的人物面前越来越弱势,我会一遍遍问自己,这是他的意思吗?把世界还给人物或者让读者当家做主而让“我”退场,这是我能为读者做的最大的努力了。
记者:据我有限的了解,在儿童文学写作领域,很少听见“难度写作”的说法。但你在一些作品里,以文学的笔法,揭示出童心的异变,儿童世界的悲剧性,并力图触及其精神内核,在我感觉里是有难度的。正如匈牙利女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用简单到极致的语言写《恶童日记》。对此,你自己怎么理解?为何给自己的写作不断设置难度?
韩青辰:不重复,希望作品饱含精神、观之可亲,追求客观与节制等,这一切常使我止步不前、犹豫等待。比如《因为爸爸》初稿写到11万字,越写越慌,只好停工走进生活。我常常会花很多时间来把我的人物和故事养活。这种血肉与共的培植过程就是我给自己设置的难度之一。
难度还来自我对自己的不满。我总是看见一支崭新、轻灵、矫健的文字大军,他们与我隔河相望,问题是我怎么渡我的河。
我相信难度会帮助我们走向更好的未知。在这方面,经典的作家与作品都做出了榜样,我只是亦步亦趋在尝试着学习。
李凤群:写作就是我和江心洲迁徙四方
傅小平:眼下盛行小长篇。但你的几部小说,无论是《大江边》还是《大风》,都是眼下“70后”作家作品里少见的大体量,而且这两部长达三十多万字的小说书名里都有一个“大”字,这看似偶然,其实也体现了你“大”的追求,在你的写作里,确乎是能见到史诗性写作的雄心和抱负的。
李凤群:我也有小长篇的,比如《颤抖》。但是最让我有感觉有劲头的还是较长篇幅的长篇小说。你说的两个长篇,确实可以代表我两个阶段的文学创作的大体模样。表面看,主要在写历时性的过往,仿佛是历史叙事,如果有耐心,你会发现,我在共时性的层面上思考得更多,也就是说,我其实是给现在写的,是关于今天的我们如何看自己如何看他人如何看来处如何看现状如何看未来……这些复杂难言的内容,我希望能有人读得出来。至于体量多大,主要与我要写的人物和问题更有关系,而不是刻意要缩短或拉长。
傅小平:你的很多作品都有一个支点:江心洲。这合乎作家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地域的诉求,但实际上也给你的写作提出了挑战,就是说,你要不断补充进去新的元素,让江心洲成为你绵延不绝的叙事王国。但从目前看,可能其中有着模式化或是重复的遗憾。那么,怎样才能避免重复,尤其是人物塑造上的重复?尤其是你在旅美一段时间后,你是否也想过让你的写作走出江心洲?
李凤群:江心洲不是一个死板的地方,对文学来说,她更像一条大船,载着漂泊的人,载着生动的折腾和无法确知的命运。江心洲让我深深领略了一个词:迁徙。这是命,这是不固化的想象的原乡。因此,不管我的作品是否还出现江心洲,江心洲让我开悟的迁徙感都会在我心里,并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影响我的写作。不是江心洲待在那里,而是我和江心洲迁徙四方。
黄孝阳:换个维度看世界,世界新鲜如橙
记者:你的创作不好概括,会让本已泛滥的文学术语,都显得有些贫乏。不过能感到你似乎在做与时代同步的尝试。从你的小说里,也能感觉到你对科技、经济、媒体等对文学,对生活带来的即时性变化的敏感。所以阅读的过程中,就像是领受了一次头脑风暴。我们通常强调技艺创新对写作何其重要,到你这里似乎得换个提法,思维的突破和创新对于写作有着怎样的重要性?
黄孝阳:换个维度看世界,世界新鲜如橙。
如果我们对小说的认识能从说书人的脸庞、巴尔扎克的风俗画等层面,进入到“另一个维度”,那么困扰我们的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这种四维空间“必然的匮乏”与“必然的终结”就不可怕了。事实上人们说今不如昔,这多半是一种情感上的表达,因为“那逝去的无可挽回”,因为“现在的普遍焦虑”。暗夜里的星光并不比千年之前更为黯淡,只要你来到云层之上。在这个被科技丈量的现实中,人,尤其需要这种能力,在一个更高的维度,重新联结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至于“突破与创新对于写作的重要性”,重要也不重要。
从个体层面来说,如果说写作是他认知世界与自我的方式(这是极重要的),而不是为了稿费或别的什么,那么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属于“陈词滥调”的东西,对他来说,也像种子从土壤里长出,就是“突破与创新”,自我突破,自我创新。从社会层面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突破与创新”何其稀少啊。
记者:与其说你是依赖于知识和技术的作家,不如说你是信赖知识和技术的作家。你的写作与其像方岩说的有一个上帝的视角,这个上帝是你命名的“生而自知之人”,倒不如说这个上帝就是知识和观念。你果真认为知识和观念,重要到可以为世界万物给出解释,可以对人的生存困境给出解答吗?
黄孝阳:知识当然重要,所谓理性之光。理性自然是有限的。爱因斯坦说:“宇宙最不可理解之处是它居然是可理解的。”但我们已经置身于一个“知识社会”莅临的前夜。
我们说人高于一切,若没有知识与观念,人也就是一种直立行走的猿类罢了。至于人的生存困境……这个问题蛮复杂的。首先,我们能意识到困境,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其次这是一个超越人认知层次的问题,与“我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一样,佛祖也难回答。哪怕有一天人类以星辰为舞台了,同样要被这个问题困扰。
但我个人觉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断认识,以及渴望摆脱困境的种种努力,为人类这个物种的进化,提供了澎湃动力。在我的理解里,知识不仅是理性思辨、科学的实证与规范、逻辑的力量等,也包括了秘索思的奇思妙想,指向直觉与本能的,通过虚构表达的诗的韵律、神话叙事等。万物因为知识有了它的名,有了逐渐清晰的面容,有了相互间的秩序,也因此有了这个我们能够寄身其中的世界。
育邦:“不合时宜“”是时代给予我最大的奖赏
记者:如果说诗歌和小说实在是太过不同的文体,那么在此次新方阵十位作家里,数你跨界最大。这么说是因为诗人和作家的思维,包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常是大异其趣。当然我不觉得诗人写小说,或小说家写诗有什么值得强调的特别之处,但一个人要把两种文体都写到相当的水准上确是有一定的难度。你怎样在两种文体间切换,这么大的跨界对你来说有怎样的得与失?
育邦:说起来,我也谈不上什么跨界,不过是心血来潮,喜欢写什么就写什么罢了。诗永远是艺术的最高形式,但并不一定要求它们必须以长短句、韵律和分行的形式来显示,通过其他形式释放出诗意也是允许的和必然的。比如,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作品,爱德华·蒙克的绘画作品,佩索阿的随笔《惶然录》,普鲁斯特的散文作品(小说《追忆似水年华》)等等。法国哲学家阿兰说,小说在本质上应是诗到散文。我想,随着时间的流逝,小说在到达散文的时刻起,它又要转向诗了。普鲁斯特和贝克特给我们做了精确的示范。说起得失,真是谈不上,只不过人们会说,那是个面目暧昧的家伙,他不该站在这里,也不应该站在那里……他有些不合时宜。我相信不合时宜是这个时代给予我最大的奖赏。
记者:赞赏你所做的写作实验,还有杨庆祥所说的那种极端的现代主义的经验,但我也担心你这样的实验性写法,会不会让你逃离现实,你的写作会不会有沦为纸上文体游戏的可能。如果说多少触及现实是作家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个提法,即你以何种独特的方式来书写你理解中的现实?
育邦:事实上,现实已然强大到你无法逃避的境地。在我们的时代,在现实面前,小说家的想象力是如此贫乏。你没有能力没有手段甚至没有意愿去逃避这个光怪陆离的现实。马尔克斯的想象力足够强大吧?然而,他所有的写作均是根植于拉丁美洲人们孤寂而又残酷的现实之上。那些有独特才能的作家,无论他们是否着力聚焦现实,他们的核心都不会改变:呈现人与世界的关系,呈现人存在的精神状况。真正的作品跟纸上文体游戏并不相关。像《等待戈多》这样的作品,看起来单调无比,由于作者贝克特自身的坚定和警醒,他的纯洁性、浓缩性和独创性成功地使文本提升为一种诗,一种艺术……其永恒的忧郁和沮丧全然发自他的内心深处,而为他的文本赢得了不容置疑的庄严和艺术确定性。我渺小,我有限……我相信我所能做的写作实践,也全然发自于我的内心深处,它们将以某种隐秘的方式呈现我理解中的现实。写作的秘密小道也将通达于广阔的世界和无尽的尘世。
曹寇:只要出现在我的小说中,“小人物”就是我的大人物
记者:很多评论都不约而同强调你写小人物。差不多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作家都把关注重心下移到小人物身上了。写小人物,写失败者是个通识,所以,问为什么写小人物是个伪命题,问写出小人物的什么特性,才是个真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虽然我不认为像张莉说的现在很多作家都写好了“堂·吉诃德”,但我赞同她说你写出了小人物身上那个“胆小、软弱和卑微的桑丘”,或可补充的是,桑丘身上还有一种近乎灰色的喜剧性,不妨由此谈谈,你写的小人物有什么特别之处?
曹寇: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小人物,或者边缘人物。这是很多评论我的文章都爱用的词汇。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写的是小人物,也不觉得谁是边缘人物,连初衷都没有。只要出现在我的小说中,他们就是我的大人物,他们就活在自己生活的中心地带。当然这仍然可能没有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真实原因可能是,这是一个基于等级社会的思维惯性。确实,我没有写过官员、大学教授、知识分子、百万富翁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我写的都是我熟悉的那类人,普通农民或普通市民,他们的社会地位都不高。因为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极其普通,普通到没有任何“艺术形象”性。
记者:你似乎讨厌谈文学性,但一般来说,文学性正是让文学区别于缺少质感,缺少诗性的一般性文字的最重要的特性。因为此,也因为你讨厌它,倒是特别希望你能谈谈文学性,或说是,谈谈能让好的文学区别于不好的文学,或非文学的那个特性究竟是什么。
曹寇:“文学性”本质是文字属性,是内在的东西,而非表面化的遣词造句。我不是反对文学性,我反对的是我们常见的那种“文学惯性”。使用文学惯性写作,有其好处,就是易于被人接受,易于获得名利,安全而有效。这种惯性的真实面目其实是惰性,是平庸,是无能。我当中学语文教师的时候,批改学生作文让我十分头疼。在我看来,他们写的文章简直没法看,尤其是所谓的好学生,堆砌词句,陈词滥调。但有个成绩很差的学生的作文,其中一个句子却让我眼前一亮,他写他的父亲,在雨天,穿着绿色的雨披,肩上扛着一袋雪白的化肥,挽着裤脚,赤着脚走在田埂上。这不仅是我看过的最好的学生作文,也是我这辈子看到的最有“文学性”的文字。因此,我要把这位学生的名字署在这里,他叫古绪超。
张羊羊:质朴和真诚,分别悬挂在我汉语扁担的两头
记者:都说诗到语言为止,可见语言之于诗的极端重要性。衡量一个诗人是否成熟、是否成功,主要就看他是否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你是否自觉已经找到了,如果说找到了,有何独特的经验、体验可以分享?
张羊羊:傅元峰说很多诗人没有自己的语言,张羊羊是一个有自己语言的人。我听后在想,我究竟有没有自己的语言呢?究竟什么叫语言?这一点上,我也无法判断。语言是个奇妙的森林,我大概可以认得出哪棵树是诗人顾城,哪棵树是小说家曹寇,因为他们的说话带有各自独特的节奏。那么我猜,傅元峰也可以从一堆诗中,听到哪首有我说话的语速和声音的特点吧。我曾说过,我写诗歌只想和朋友们说说话,因为很多诗人连话都不好好说了。
我的孩子两周岁多的时候,有次给他吃鱼。刚吃完一口就号啕大哭起来,这让我有点莫名其妙,我问他为什么哭呢?他指着被我夹过一筷子的鱼说“鱼破了”。那一个瞬间,我被孩子的纯真感动了,他的难过源自人性最初的善良。然而,鱼破了——这个短句是多么美妙的诗性语言啊,我再也找不到这样三个字的组合——这也许是我一直在努力寻找的语言。
记者:霍俊明说张羊羊“是一个试图反复擦拭玻璃的人,反复写给过去一封信”,挺有意思。你的写作或许如他所说更多带有封闭性,有助于提升诗歌的纯度,但也会缺少包容性和复杂性。从我个人的观感来说,现代诗歌似乎已无法重现过去年代里的那种简约、简单,因为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的诗人,不得不处理一些比过去年代复杂得多的经验。你似乎是反其道而行之,何以如此?
张羊羊: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我诗集《绿手帕》的自序来回答:我特别喜欢故乡田野上的一种小花,蓝盈盈的,仿佛一直对你眨着眼睛,她们就像一群双眼皮的女儿。她有一个很老的名字:婆婆纳。也是,每一位慈祥的婆婆都会回到孩子,她教诲我一个词语:质朴。我还喜欢故乡田野上的一种鸟,在农业中国的东部,它从谷雨开始就会啼叫。它的名字叫布谷,我觉得,庄稼就是被它催熟的,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诚实地书写着麦子与稻子这两类伟大生命供给的及时交替。它教诲我另一个词语:真诚。这两个词语,分别悬挂在我汉语扁担的两头。所以,我去了许多的远方后可以明白,出生的地方最适合播种汉字。我是一个依靠记忆写着的人,也是一个依靠记忆活着的人。越来越喜欢简单了,于是写诗也越来越简单了。它们的性格慢慢长成了我多年前的一句诗——像我轻声的歌唱,为自己的孤独壮胆。推开每一扇门,记忆就会轻声说话,我的小时候就回来了。
孙频:文学最忌讳盲目模仿,作家应找到最适合的写作方式
记者:你是这次“文学苏军新方阵”里唯一的“80后”。从年龄段上说,的确是够新的,非常新。你的写作给人的感觉也是别具一格的“新”。由你来谈谈对“新”的理解,也是再合适不过的。
孙频:在江苏文学这次新方阵里我是年龄最小的,所以看起来似乎就“新”了一点,其实写作时间也有十年了,根本不算新人了,从写作风格上来说,我小说中或许确实有一些独属于我自己的东西,这种独特的风格会给人比较新颖的感觉,但也并不是无源之水,所有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源头,或者是前辈作家们一代又一代的影响,或者是源自自己的童年经验,独一无二的成长经历,但因为所有的人性都是相通的,所以无论怎样独特其实都是有限的,都是遵循着文学的基本规律,人性的基本规律。
记者:约略读过你两三篇小说,读的过程当中,我会不由联想到金基德的电影。感觉你写的不是那种普遍可以揣度的经验,但你刻绘的文学氛围又特别真实。从这个角度,借用保罗·奥斯特一本书的书名来说,你的写作有点像“密室里的旅行”,把“密室”写好了,剑走偏锋推到极致,实在是一种高超的技艺,当然走出密室,去看看旷野上的辽阔风景也不错,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孙频:因为文学的生态是极其丰富和多样的,又极其个性化,就像热带雨林一样,各种植物都可以生长,很难用一个既定的模式去概括作家们的写作方式。因为出生地,生长环境,性格,阅读量等各种方面的影响,有的作家是开阔的,厚重的,可俯瞰大千世界和百态人生,作品也磅礴大气。有的作家是向内的,幽闭的,但也是更为纵深的,比如卡夫卡,比如普鲁斯特。我觉得文学最忌讳盲目模仿,一个作家应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式。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