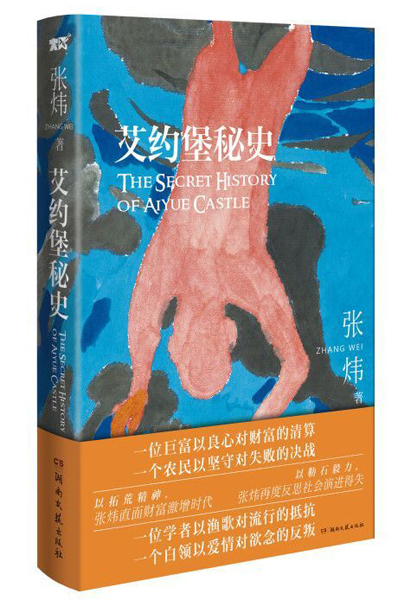
《艾约堡秘史》 张炜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午九时,蛹儿来到了花君的领地。这头浅棕与白色交织的花斑牛温良和善地凑近她,一边咀嚼一边直视。有一股青生气并混合了草莓的香甜扑面而来,她忍不住抚摸它的额头。当她的手指触碰到那密密的金色睫毛时,它就依偎过来。这样站了一会儿,她回到隔间,一眼看到了未能放到柜子里的半瓶酒,还有案上的杯子。这说明淳于宝册来过这儿,而且极有可能在深夜无眠时光顾过。那是他面对花君的独酌。坐了多久?他有慢品的习惯,半瓶酒至少需要一个小时。她收拾着留在案上的东西,小心地拭去一点红渍。她接通了领班,询问董事长何时出门,对方说用过早餐就回自己房间了。
淳于宝册午休的时间稍长,下午三点多招唤蛹儿过去。她第一眼就被这个人的憔悴吓了一跳:头发没有梳理,双眼布满血丝,胡茬没有刮过,嘴唇挂着焦干的白屑。他的呼吸里有一种霉味儿,就像刚刚吞食了一枚烂苹果。她明白了,他是昨夜到花君那儿的,有什么心事搅得他睡不着。而这个人的睡眠之好是有口皆碑的,都知道他想睡就睡,这正是保持强健体魄的主要秘诀,瞧那一头微鬈的黑发,仍然像年轻人一样致密,闪着石墨的幽光。他嗓子有轻微的沙哑:“今晚上我要宴请一位,不,两位重要客人,你和我一起吧。”他嘴角那儿颤了一下,眼睛转向一边。“嗯。几点出门?”“就在东厅那边。”蛹儿忍住了惊讶,因为她不记得有过这种情形,他会让她出现在那样的场合。她垂下眼睫,想说一句“我害怕”或“我担心”,最终还是咽了回去。她明白所有言说都是多余的,只需遵命。“你今晚要穿最好的衣服,那件浅绿色有金线的套装。”他看着她,神色慈祥而又沉重。她愉快地点头。不知为什么,她对即将来临的这场晚宴有点不安。到了傍晚四点多钟,这种不安又变成了惧怕。
为了舒缓一点紧张,她开始关心不需过问的一干屑琐,叮嘱了几遍领班,还要来菜单看了。菜点过于简单,西式,实在说不上丰盛。所有的灯都亮起来,艾约堡的盛装除了华贵的灯饰,再就是无处不在的深沉的檀香气,这种香型是董事长亲自选定的。蛹儿踏上长廊的第一步,就从变得越来越浓的气味上,得知即将开始的是一个难忘的夜晚。淳于宝册已经站在长廊一端,不知是等她还是独自冥思,直到她走近了才抬起头。她发现他已经好好打理过了:头发齐整,修了脸,眼中的血丝也消退了大半;穿了笔挺的藏青色西装,领带是酒红色的,整个人不像平时那么洒脱,却足够庄重。下巴那儿有隐隐的一处疤痕,这会儿显得清晰。她想去搀他的胳膊,但他好像要故意保持一段距离,一个人走在前边。
领班锁扣已经在二楼等候了。这儿的一间西餐厅一年里用不了几次,记忆中还是去年中秋他在这儿宴请堡内的人,他们是主任和领班、两个速记员,全是女的。那个夜晚他与大家饮酒,吃月饼和干果,打开东窗赏月,兴致很高。长条西餐桌铺了亚麻布,有枝型烛台,壁炉也点燃了,银餐具闪着迷人的光亮。这一切蛹儿以前只在荧屏上见过,这会儿将兴奋隐藏起来。这里是东厅最讲究的地方,无论使用与否都要保持高度整洁。蛹儿发现整个堡内没有一间餐厅摆放传统圆形桌,也没有一件雕花硬木家具。即便是董事长自己使用的那个小厅也是西餐桌。今夜,这间常年闲置的大餐厅烛光闪闪,壁炉象征性地燃着几支劈柴,驱散了微微的秋寒。蛹儿等待着,留意楼内所有的声息。到处一片安静。
夜幕降临了。蛹儿在东厅陪了一会儿淳于宝册,忍不住走出大门。身穿灰色制服的门童左边的耳朵动了一下,转过脸庞:左边传来一阵引擎声。随着粗糙的摩擦颠簸声增大,一辆破旧的蓝色出租车叹息着拐到坡道上,费力地爬到门前。门童的白手套还没有挨近车子,里面的人已经敏捷地推门跳出。蛹儿的目光最先接触到的竟是那双刚刚沾地的脚:穿了不合季节的人造革凉鞋,没穿袜子。这人一下车就弓身为后座开门,所以一时看不清他的脸。一男一女两个人走入门前光晕中,蛹儿惊呆了。男子有五十左右,清瘦,戴了眼镜,有些短的夹克袖子中露出了一双触目的大手。他旁边是一位不足四十的女人,肩上背了带子长长的挎包,微笑的长脸庞上是一双心不在焉的、分得很开的眼睛。两个人好像刚刚从田野上跋涉而来,这会儿稍有不适地看着灯光下的建筑。蛹儿上前做了自我介绍,欢迎他们来艾约堡,在前边引路。男子进门前在垫子上蹭了蹭鞋,还扶了一下眼镜,礼让身后的女子。
淳于宝册已经等在前厅,迎上来握手。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男客人身上,寒暄的时间稍长,有些喜出望外的样子,紧紧攥住那只比他大一些的粗手。两只手松开后,主人好像迫不得已地转向女子,点头微笑,说了“幸会”两个字。女子耸了耸挎包,那过长的带子别扭极了,一对散散的目光渐渐收束到主人脸上,重复了对方说过的短语,点点头,把垂到额前的长发拂到后面。淳于宝册好像更急于介绍旁边的人,明显提高了声音对那个男子说:“这是我们蛹儿主任,哦,就是这里的总管了。”他松松地揽住蛹儿的肩膀,将其拢到离客人很近的地方:“这是吴沙原先生,矶滩角村的领导,年轻,了不起……这一位是民俗学家,著名学者,她的名字你一下就会记住的!”话刚落,那位女子对蛹儿点头,递上自己的名片。
蛹儿低头看了一眼,深深地记下了那三个宋体字:欧驼兰。同时她脑海里漫洇出一个遥远而荒凉的图象,并感到一丝焦渴。一片无边无际的荒漠,一只骆驼在跋涉,然而,突然出现了一蓬碧绿的兰草。她双唇蠕动,看着这位陌生的民俗学家,一位突兀地出现在面前的女子,心口慌乱地跳了几下。在明亮的灯光下,她这会儿更为清晰地看清了对方:稍高一点的个子,长腿,下身着粗布裤,上身是一件宽松的藕荷色外套;敞怀,浅色针织毛衣下伏着小小的一对;最让人难忘的是眼睛,仿佛一直在走神;双唇也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它显然是最温软最可爱的部位,一旦开启就会有迷人的吐露,不过大部分时间是沉默的。蛹儿由她想到了一种动物,准备以后告诉董事长。主人是给人取外号的高手,这种习惯和能力已经深深地感染了周边的人,特别是蛹儿,每见了一个生人都会将其想象成一个什么动物。
淳于宝册与客人在东厅坐了不到十分钟。这是正式晚宴前的一段交谈。两位客人第一次访问艾约堡,对这儿的一切,从气息到各色陈设却没有表现出多少讶异,就好像待在了早就习惯的环境中,比如仍旧置身于那个叫矶滩角的小渔村。蛹儿隐隐觉得主人将自己呼唤到这两人身边来一定要派作什么用场,而从客人出现至今,她仍然感不到一点用处。至于这一男一女,他们对于艾约堡和它的主人又会有何价值?她细细观察了他们,认为这个女子神情特异,大概就因为那双无法形容的眼睛,一张脸庞显得生僻而又迷人。不过这人如果是有名的学者,还不如说是在野外出没的地质勘探员,她从前见过这一类人。那个男人比以前熟悉的村头稍有不同,清瘦,一看就知道是常年于室外奔波的人,皮肤被风砂打磨出异样的色泽。最可笑的是有一只眼镜腿坏掉了,临时用胶带粘了一下。他脚上那双过时的黑色凉鞋空隙中闪着粗笨的趾头,它们在翘动,这让她生出一丝同情。
淳于宝册努力使自己放松下来,可是有些颤抖的嗓子说明他最后也没有做到。蛹儿甚至不敢盯住他看。好像董事长正在别人的客厅里做客,竭力适应着什么,掩饰着深深的不安和艰涩。好在这段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他做个手势站起,与客人步出客厅,往二楼走去。两个男人走在前边,蛹儿陪女客走在后边。上楼时她抬头望了一眼董事长沉沉的后脑、有些弓的后背,仿佛有一只手掌在心口那儿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她为了镇定自己,在扶手上倚了几秒,然后若无其事地向前,两眼盯着脚下,生怕绊倒。楼梯毯是沉闷的酱红色,实在太厚了。
蛹儿好像解开了许多天来的心结,胸间豁亮起来,似乎明白了走在前边的主人发生了什么,遭遇了什么。一切都与这两个客人有关,不,严格讲只能是这个欧驼兰,是她让董事长遇到了一个坎、一个麻烦。蛹儿觉得这件事尽管古怪到极点,但它的确发生了,而且两个主角都在眼前。至于整个事件从发生到现在过去了多久,缘何到了时下一步,却完全超出了她的想象。她料定今天的晚宴是主人精心筹划的结果,也许这之前已经耗去了他的许多心思。想到这里她不禁疼惜起来。她知道像这样一个坎坎坷坷九死一生的人,再也经不住任何颠簸了,如果那样,老天对他就过于残酷了。
她最担心的是他能否熬过这一场,再次加重身上的病:那对艾约堡来说简直就是灾难。她来到他身边的三年中,曾亲眼看到他三次发病。这种严重的疾病尽管在这之前由他亲口预告过,但一朝爆发起来也还是把她吓坏了。一个如此严谨理智深谋远虑的人,发起病来竟然无所不为,狂躁骇人,几乎完全不能自理,变成了堡内一头巨兽。这期间只有几个人能够接近他,集团内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遮掩秘密,心照不宣,心惊肉跳。三次发病都在秋天,大约是季节的变化再加上某些刺激,通常要经过一个多月痛不欲生的煎熬才算过去。为他诊治的是高薪聘用的一位老中医,老人使出浑身解数为他缓解,却无论如何难以根除,甚至无从判定病因,最后只好使用三个字加以概括:荒凉病。蛹儿对这个命名钦佩之至,因为她深知病人在那个时刻有多么“荒凉”。
眼下又来到了凋零的秋天。蛹儿心口那儿一阵抽疼,长时间挪不动步子。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