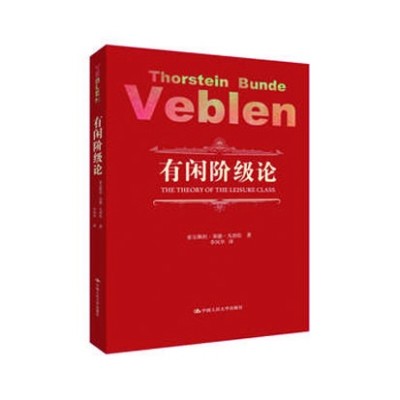
《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 [美]托斯丹·邦德·凡勃伦 著 李风华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
■刘金祥
在书籍泛滥的时代,有些书看一遍也许足够了,但有的书阅读多遍仍不肯释手。笔者由于参与某项课题研究的缘故,对美国著名制度经济学家托斯丹·邦德·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研读了多遍,但使我多次捧读此书的原因,并不完全是为了完成上述学术任务,而是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主流思想互不相容、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冷战时期,中西方经济思想史上褒贬不一的经济学家的确为数不少,譬如哈耶克被社会主义阵营的学者视为捍卫自由思想的勇士,被资本主义营垒中的专家讥讽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叛逆,这种评价上的巨大反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个阵营政治对抗的需要。但在经济学发展史上遭到两个敌对阵营同时诟病的经济学家却寥寥无几,而凡勃伦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凡勃伦作为制度经济学肇始者似乎已成定论,但以笔者之见,如果用意识形态审视“制度”一词,那么,将凡勃伦看作“制度经济学”创始人,可能有些牵强。诚然,凡勃伦一直主张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也必须是人类经济活动所赖以实现的各种制度。但在凡勃伦的学术体系里,制度是由思想和习惯涵育而成的,而思想和习惯则源于人类的本能,这种本能又被凡勃伦分为三方面:父母天赋、工作本能、个人好奇心。有鉴于此,凡勃伦关于经济的分析和阐述,从表象上看是针对各种制度,而究其实质则是对人的本性的阐释和对人的本能的抉发,质而言之就是对人性的勘测与解剖。而这种基于人性的经济分析却不是凡勃伦的首创与专利,当初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理性揭示,就是以“人是自利的动物”这一人性论的核心观点为立论基础的。
在《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一书中,凡勃伦以似乎来自西方世界的彻底超脱的眼光,真正给东方世界的人类生动地描绘了一个诡异滑稽的社会。依照凡勃伦的观点,人性视角下的当代人与他们未进入文明界域的祖先相比,在本质上并无差别,而只存在形式上的不同。这种人性就是:期望借助掠夺手段无偿占有别人财富,而不愿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这种人性在野蛮社会中的表现就是:哪个人哪个群体越强悍,征战的土地越大,杀戮的对手越多,抢劫的财物越丰厚,哪个人哪个群体就越容易获得人们的尊敬,而掠夺者也志得意满地在其营帐上高悬战利品以示其坚强和勇武。在凡勃伦看来,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人性中这一丑恶因素依旧没有根除:有闲阶级在精神上仍然传承着古老的打劫方式,并对非直接劳动掠夺来的大量金钱进行挥霍且对这种残忍的掠夺方式加以炫耀。相形之下,依靠纯粹的劳动付出获取财富却成了一种耻辱,而且社会是不可能给单纯出卖体力劳动的人以相应报酬的。但人们尽可放心的是,这样一个与文明完全相悖的社会是不会爆发革命的,因为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无论是雇佣工人还是资本家,都期冀通过盘剥他人以告别体力劳动这种“耻辱”,都渴望通过不劳而获地取得巨额财产来比奢华。所以,处于社会底层的草根只要有哪怕是最可怜的生存条件,也会趋之若鹜地向富商巨贾们学习效仿;他们日夜思考如何膜拜有闲阶级,如何成为有闲阶级,而绝不是整天惦记着进行暴力革命。也就是说,无论是有产者还是无产者,都没有摆脱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罪恶基因和恶劣人性,这也许就是人性的宿命,也是整个人类的悲剧。
凡勃伦的上述思想观点被现实社会所不容,他始终恪守的中立的永恒的人性论,使得他的思想观点同时受到来自左右两翼的批驳和攻击,尤其是有闲阶级不会给凡勃伦思想以任何传播的机会和渠道,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上,还没出现过任何一部书比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更加尖锐、辛辣地揶揄和讽刺贵族们的生活,所以,西方有闲阶级攻击凡勃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者”。那么,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又是如何看待凡勃伦的呢?他们不仅没有将凡勃伦吸收进自己的队伍,相反倒认为凡勃伦是个比堂而皇之的资产阶级更恐怖更可恶的隐蔽的敌人。凡勃伦成为两面不讨好的争议性人物,成为中西方两大阵营竞相攻击的对象。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化思想观念的冷战年代里,凡勃伦及其理论学说无疑是个个案。
事实上,无论是褒贬不一的哈耶克,还是腹背受敌的凡勃伦,我们的困惑和疑虑并不在于中西方的当代学者对他们的思想作了什么评价,而在于怎样解释会出现这样的评价,特别是怎样理解这样的评价竟然出现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中就曾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本质上讲是一门历史科学。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也提出政治经济学是对历史负责的一门学科。假若这种观点有其科学性,那么评价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及其学术观点,究其根本就是对历史的评判和裁断。克罗齐和汤因比两位思想巨匠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学术声誉不亚于汤因比的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得更加直白贴切:一切宏观历史都是自传。所以,评价具有历史科学属性的政治经济学,如同评价历史本身一样,结论的不同所反映的无非是同一时代不同阶层的人和不同时代同一阶层的人生存状况的不同而已。科学发展基本规律与内在逻辑提醒我们,学术研究摒弃这样一种现象:某个学者的评价非常正确而其他学者的评价极为错误,因为不同结论的出现均是出于同一原因——所提出的问题迥然有别,所给出的答案自然大相径庭,但历史的真相始终只有一种也只能有一种。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哪种语境下的凡勃伦都是同一个凡勃伦,绝不会因为评价的分歧和结论的差异而出现两个或若干个凡勃伦。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以人性论为基石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时,只是考虑到那个历史阶段无产者对有产者的激烈抗争并试图使自己的理论学说超越这种激烈抗争,但他并未充分地意识到这种激烈抗争的尖锐性、残酷性和不可调和性,更没有意识到这种尖锐性、残酷性和不可调和性,最终会将他的理论学说推向如此难堪、如此尴尬的境地。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