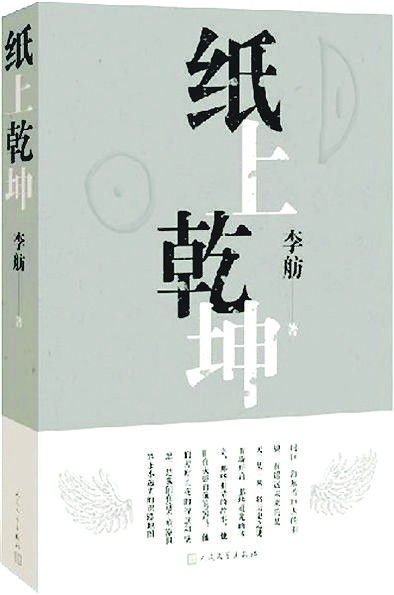
大文写作的难度和风险在于,你是否给予了大文以高大的比重,就是说,在你文章的大盘里,是否富含了相匹合相对称的厚重、深邃和新知识。就散文而言,是具有散文艺术性和散文价值观的厚重、深邃和新知识。
一
在散文一本一本叠浪涌来的呼啸中,《纸上乾坤》裹挟其中,不声不响就到了面前。哑默了好一段时日的我,读了《纸上乾坤》(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心头一个激冰,又一个遽热,觉得有话要说了。
曾几何时,在反假大空的群情激奋的集体语境中,文学的大军纷纷转向,一窝蜂地趋于个体观照、家族叙事、地方实录等向度上的聚焦,在细碎、微小的毛细血管上使大劲抡大锤,以实现自己对文学可能性的认知价值,并藉此创造被文学史书写的机会。春来秋去,地盘热了,热得炙手,热得反衬出了另一块地盘的冷。而文学的存在,文学的功用,恰恰是给世界以温度——恰恰是寻找到被遗弃的僻地、死角和不胜寒的所在,一字一句送去自己的炉火,尽各种可能不冷落任何一个地方。但逆众而行、逆即时性潮流而行,是有难度的,也是冒风险的,它要求你用一己之力与时间拔河。因为,今天的对错、是非,不是今天说了算。所谓胜利者,即是对未来的正确的预知者,反之,为失败者。左一下,右一下,在一左一右外力的夹拍、扇动下的纠偏行动中,在风声和反冲的作用下,创生了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事物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大道前进的不二法度。
《纸上乾坤》及其作者李舫很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并从集体的朝拜似的写作炫影中脱身出来,找到了只属于她自己的那盏无影灯和广大的着陆点。纠偏,成为她正说的叙事策略与写作文格。
从书名即可看出,大,是这本书高调标榜的一个符号,一种尺度。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以中原为核心的218万平方公里,是春秋。生发了战乱杀伐、礼崩乐坏,更生发了以孔子、老子、墨子三大哲学体系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是春秋。但这只是狭义的春秋。李舫的笔左右概括、上下包揽,墨迹所至,古今五千年,一去千万里——这是她心中的大春秋。
二
综观李舫散文的成形路线和与同道的分野界划,我以为,似可将其称作大文写作。大文写作愿意与高大上为邻,却更愿意是对大词写作、假大空写作的不屑。
大文写作的难度和风险在于,你是否给予了大文以高大的比重,就是说,在你文章的大盘里,是否富含了相匹配和相对称的厚重、深邃和新知识。就散文而言,是具有散文艺术性和散文价值观的厚重、深邃和新知识。我们知道,ρ=m/v,即比重(相对密度)ρ与体积v成反比,与重量m成正比。为什么那么多人热衷于写小——写小事象、小题材、小人物、小情绪?这是因为与重量一样的文章相比,他获具了大值的比重,与比重相同的文章相比,他收揽了更显明的厚重。他们是在用一个重字,去拼命博一个尽可能大的字。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写小的,就一定写出了高密度和厚重?写大的,就虚胖、水肿,又轻又薄,扛不住时间的风,稍稍一吹,就去了乌有国?当然不是的。考量一部作品,必须考量其重其大的合力和互融综合效应,此处的大,是在各个维度上的大,包括指向内心尤其人心深度矢量上的大,而不是单一的大。就此,李舫用一部“大春秋”的出场,给出了证据链清晰而结实的回答。
说白了,李舫的大文写作,就是在写大事象、大题材、大人物、大情绪的大文章过程中,朝着空茫夜海中熹微的目标桅灯,调动包括无限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以及思想、哲学、文学教养在内的一切资源和手段,去坐大坐实散文的生成边阈。她调动的那些元素,即是她为增加作品厚重和深度而强力压入大地内部的比重。她的工作是,面对一座广大的矿山,在每一个开挖面和点炮的位口,将A浅→A深、B轻→B重的迁移和突进的战斗进行到底。再有一点,李舫大文写作中的大,更多的是大势的大,是对时间大局不可逆转的总趋势的正确把定的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她的大文写作,也可谓之大势写作。《吕氏春秋·尊师》有言:“有大势可以为天下正矣。”我们把这句古语换个立场讲,那就是,大势写作可以写出一片散文江山。
读散文的“大春秋”,何尝不是读作者才识的大春秋。
作者的语言文字有很高的辨识度,冷凝的玉的品质,蒸发的血的热度,格言警句似的哲思,排比句的诗意引申与深入,剞劂的锋利,简练、清洁、干脆,如果以美文来称道,我以为恰恰是对“李舫体”文字的失敬和轻薄。对古文古诗词的信手拈来,对四个字一组的词链的呼应与嵌入,更是加大了她语言的个性化敷设。翻译外文的偏业,让她打通了中国与外国之间尤其是与西方世界的关节与机杼。《纸上乾坤》若不够大,《纸上乾坤》若没有一条大道,还真不能装下各文体各文本的诸子百家般的大著述、大演讲、大辩阋,和大奔走。为了在限定的文字体量里凸见大文写作的要义,很多时候,作者都必须在针尖上修筑广场,将小我的身影隐匿在文字的水银镜背后,只让那个全知全能的神代她巡山和说话。
“一个人必须为创作激情的神圣天赋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一规律几乎很少有任何例外。”(荣格《诗人》)不用说,正是作者努力呈现的才气的、识见的大春秋,加大了散文《纸上乾坤》的比重,实现了自己用重去深狭、用大去宽广的脉向与抱负。
而这一切,无不得益于作者的大格局、大眼界、大气象,和作为大报记者置身高站点的得天独厚的在场、敏见、思考与闪电行动。
《纸上乾坤》中的主体作品,仅从外象看,无论写人叙事,一眼就能看出它们的大。要么是国家层面的大。如,写大宋王朝在景德元年以大国身形力挽狂澜的《大道兮低回》,写老子与孔子见面和面对面的口舌辞锋与思想交汇的《春秋时代的春与秋》,写春秋齐国吸纳了众多学人的稷下学宫流变的《千古斯文道场》,写中国远征军在腾冲喋血抗日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写巫峡始源与文化变脸的《飘泊中的永恒》,写夜郎国勃兴与衰亡之秘的《追寻夜郎》;要么是家国层面的大。如,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诉求和人生认知的基本面上,写韩愈贬任潮州刺史后的作为的《在火中生莲》,写我与故乡呼伦贝尔血脉情结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写任继愈与季羡林致学报国的《丹青一抹光淋漓》;要么是业界向度尤其文化向度上的大,如,写画家、雕塑家、作家、学者和开化纸的《弗里达:不安的缪斯》《“蓝骑士”——康定斯基在公元1917年》《“我神智健全,我就是圣灵”——记文森特·梵高》《贾柯梅蒂:青铜魔法师》《墨点无多泪点多——堂吉诃德和他的〈堂吉诃德〉》。
三
李舫在作品中,以学人的严谨叙写、文人的深情抒怀和记者的全角评说的夹叙夹议的方式,以人物故事的倒钩打进和切入主题的卯窍,拉开大幕,尔后大捭阖,纵横古今中外天上人间,拉动和驱使作品的大磨向着主题的场域作螺旋状的上升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作品散发的气息,无不是关涉对万物的悲悯、苍生的关怀、生命的热爱、美好的追求,和对浩然正气的养植。就历史文化大散文而言,除了这些气息,还有时间结晶的盐将自己的智慧和经验,传给当世去借鉴、来启发。
《能不忆江南》针对的是古城杭州,不可谓不大。文章从哥伦布下海写起,再丝绸之路,再托勒密、鲁布鲁克、鄂多立克、马黎诺、利玛窦、范礼安,然后回到中国,回到五千年前的良渚人、良渚文化,最后一笔荡到明代杭州天灾,明孝宗出手相救,写了半天,围着杭州绕了一圈,也没敲开杭州今天的城门。但这正是一位理性的写作者对牛顿第二运动定律F(外力)=m(质量)×a(加速度),和物理算式v(末速度)=v(初速度)+a(加速度)×t(时间)的由定性趋向定量的景从与跟进:跳出眼前的城,跑得远远的,才能在高远的地方把一座大城不留余地俯瞰、尽览,才能让恒值的加速度,在更长的时间更远的距离上,变为最大的速度和最有效的冲袭,去完成破城读城的预设。一路写来,一直进城,一直进不了城。没错,李舫正是用这个魅力四合的文本,向卡夫卡的《城堡》致敬。你看,为了比重的格值,李舫竟可以把老外的小说拿来,放在中国散文的秤杆上。
其实,说了一大箩筐话,我不是扬此抑彼,以数落小的不是来褒美大的是,我只是想说,面对文学的大蛋糕,我们可以这样下刀,也可以那样使勺,只有广开言路,共执槷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迎来春秋那种穿过童年时期的人类文明的黑暗大走廊,在仰望星空的沉寂中,乍现的思想大爆炸、文化大繁荣、社会大进步。这个,才是大事,更是大势。
令我惊讶和犯惑的是,李舫的作品中,几乎看不见性别的招展——这与那些不拿身体器官说话,不拿闺阁那点私事说话,就没有话可说的女性写作者形成了莫大的对比与有趣的反讽。但收入书中的两件有着散文诗的语美和换气方式的作品《也无风雨也无晴》和《易水寒》,还是在不经意间,出卖了作者李舫对待朋友的情谊和作为女人的柔情百结的底牌。
尼采说:“我一切的著作都像是鱼饵:也许我像任何人一样,非常了解钓鱼之道?但是如果没有钓到什么,不要责怪我,那是因为没有鱼可钓。”(《超善恶:未来哲学的序曲》)而我看见的事象是,《纸上乾坤》还在试水,鱼已游来,不是一尾,而是一群。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