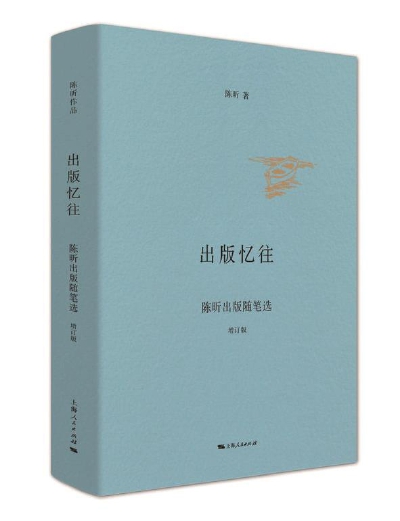
《出版忆往:陈昕出版随笔集(增订版)》 陈昕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
孙甘露
2007年,上海书店出版社计划出版我的作品系列,并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组织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就是在那次会上,我得以有幸认识陈昕先生,并聆听他对我的写作以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诸多观察和判断。后来我得知,陈昕先生事先嘱咐出版社为他准备了我的作品和相关材料,并为参加会议亲自撰写了发言稿。
这件小事多年来一直在我的记忆里。在此之前,对于上海出版界,我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出版的书籍上,对于出版业所知甚少,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留意陈昕的文章,也因此注意出版物在它问世的同时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关联。这是那次作品研讨会给我带来的饶有意味的启示。实际上,也因此使我得以从出版以及更多的角度,反观写作,这也是陈昕在多处文章里提到的,如何从文化的传承、学术的研究、社会生活的迫切要求中发现出版的焦点及重大命题,并以自己的实际工作来响应时代的呼唤以及出版传统的接续和发扬。
在我读来,这本文集的重心有二,一是对汪道涵、夏征农、王元化、陆谷孙、巢峰等老一辈专家学者的生平交往的回忆,同样,这些学术出版、学术研究所形成的交流和思索,无疑是构成陈昕出版生涯极其重要的方面;另一方面,在陈昕从事出版工作的前期,与一众年轻学者的交流促进,也是那个时代年轻一代学子,对中国社会经济急剧转型时期思想领域各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敏锐思考,构架了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的探索之道,而经济领域的大量问题,不论在学术上还是实际经济活动中都是当时社会思想领域最为急切需要回应的。这是出版人如何主动参与塑造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的很好的例子。
如同陈昕在《铸就历史的铜镜》一文中论及学者的品格时所说的:大学问家自当具备“通家气象”,学术视野广阔,境界高远。在他的运筹中,“通”者之首义为“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其始终,查其源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通”者必须“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我想,这也可以视为陈昕在大时代背景下对出版事业追求的自我期许吧。而这也可以视作所有从事与文化相关工作的人所向往的目标和方向。
作为一个在文化单位供职多年的工作者和写作者,读陈昕这些文字平实、内容丰富的文章,经常有会心的瞬间,感触良多。时移世易,那些不懈工作的时时刻刻,那些殚精竭虑思索的日日夜夜,由一篇篇文章,一本本书所构成的人生,就是我们给这个世界的最忠实的答卷。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