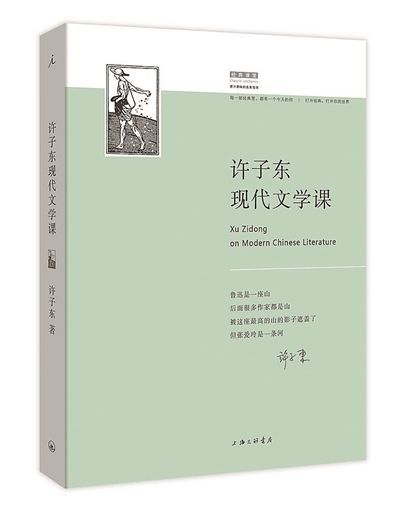


许子东
6月15日,《许子东现代文学课》出版,香港岭南大学许子东教授开启全国范围内的读者分享会,所到之处读者的热情可以让任何一个严肃的文学学者惊讶。
8月16日,许子东回到上海,讲座就在他当年投稿的《上海文学》所在地——上海市作家协会,巨鹿路675号爱神花园。当年,他也曾在同样的地方坐在下面听王元化、高晓声先生的讲座,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场景。
大厅旁边的小房间,许子东说还是第一次进来,墙上挂着从夏衍、巴金到王安忆的黑白照片。“那个地方以前是‘文革’时巴金打扫的厕所,现在已经没有了。”他指着房间外不远处的一个地方说道,从那里可以看到旋转楼梯,很多年以前,他就是沿着它走向《上海文学》编辑部,就像步入一座艺术的宫殿。
大厅里挤满了人,很多人举起手机,准备拍照,据说这是近些年上海作协大厅人数最多的一场活动。活动开始了,许子东从夏衍、巴金的照片前走过,进入大厅,现场一阵轻微的骚动。他面带微笑,调侃自己正在进行一场“巡回演出”,这是第五站,“钱钟书先生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这只下蛋的鸡呢?可是现代社会不一样,是要母鸡出来秀身材,那么多作家来书展,全部是母鸡,蛋早就在那里了。”
讲座后的第二天,许子东在上海接受了北青艺评的专访。
现代文学的“香港视角”
北青艺评:说到“鸡”和“蛋”的关系,突然想到李欧梵老师也有一个说法,他当时说再也不想参加书展了,感觉作家被“消费”得太过厉害。他当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警惕作家的“明星化”,您怎么看?
许子东:现在出书好像变成了一个程序,尤其你想让你的书多印一些的话,作家必须要参与一些宣传。这不单是书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化工业的问题。印刷工业在目前的文化工业里面是弱势群体,是在往下走的,所以我有些理解这样的做法。李老师的抱怨是很奢侈的。现在的情况不像80年代,写东西写完以后,人家给你写书评是真的喜欢你的书,今天的很多评论都是约稿的,都是有策划的。这样做的坏处很明显,大家一般都说好话,没有真的批评。所以现在整体上没有文学批评,现在都是文学表扬、学术表扬,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是生产链的一环。
北青艺评: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其实是知识分子和传媒的关系问题。孙郁老师曾对您有个评价,他说,“许子东是学院派里的活跃思想者,但使用的是非学院派的方式去表达。”一方面,我确实对现在所谓的纯文学学院派自说自话的氛围心怀不满,另外一方面,也觉得“明星化”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方向。
许子东:以前我们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现在是酒香也不能巷子深。我这次一路打书,还是很感动的。你这个文学的“鸡”还有人来看,这就已经不错了。另外,就是你讲的问题,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浅入深出,保持学术水准,不能为了有人来看而说话变了,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是我跟陈平原有过讨论,平原说只要你对着传媒就会变声,我说不一定。然后我在《锵锵三人行》里尝试,不能说的话我不说,开始他们觉得我是对节目的破坏,你上来又闷,长得又不好看,说话又不好笑。窦文涛最早的时候跟我提要求,每次来要准备两个笑话,我才不理他,其实我开始真准备了,准备以后我觉得,我干什么呢?我有啥好处呢?要说我的话我才做。时间久了以后我发现没事,人家照样能够接受。回到你的问题,作家“明星化”?主要是不能为了传媒改变作家的立场,你再“明星化”那也是一个作家,你的创作不能受影响。
从这本书来讲,如果跟别人不一样,也许就会有一点学术价值吧。最简单地说,我跟北京学界传统看法不一样,跟夏志清也不一样,有同行看了说有“香港的角度,还有你自己的观感”。所有重要作家“鲁郭茅巴老曹”,我希望都有自己的看法,现代文学的主要学术论争我也都有所涉及。当然这不是文学史,是针对学生讲课,有时是即兴联想,资料细节可能不如集体写作项目般严谨,有时不能讲得很深,只是点到。但愿在那么多文学史和现代文学教材之中,我仍然有我自己的看法。
欢迎大众关注,有误解也没关系
北青艺评: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本书的“香港视角”,对很多作家也都有不同的解读。郜元宝教授曾说,“现代文学史没有故事”,陈晓明说,许子东将故事完美地融入了对作家、对理论的探讨之中。同时,我们也不可避免听到一些质疑的声音,一个知识分子在面对大众发言的时候会冒着很多风险,“浅入”大概很多人能意识到,但是“深出”的部分未必能注意到。
许子东:这个学科我其实比较熟悉,所以想把很复杂的问题讲得简单一点。首先,欢迎大众关注,有误解也没关系。行家,如果仔细看了,可能也会明白。王德威的评论,是因为他很清楚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史观和海外学界的鸿沟与区别。更不要讲,现在还有一些“新理论”,所以他们认为我站在香港的角度、以个人的角度去说就会有学术分量。
北青艺评:谈到教师的责任,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一个教师应该做的不是去充当学生的精神领袖,而是尽力做到“知识上的诚实”,你在讲课中是如何去平衡这种“自我观点”的表述?
许子东:我给学生讲课分三步:第一步,你什么都不要看,先看作品,不要先看评论,这是我的一个哲学,直接读张爱玲、鲁迅、郁达夫;第二步,我讲的大部分内容是别人的,这是我作为一个老师的责任,传授知识。王瑶怎么说、唐弢怎么说、竹内好怎么说、钱理群怎么说、李欧梵怎么说、夏济安怎么说;最后一步,我说,下面是我的看法,考试不考。我认为A胡说,B有一点道理,C我认为讲得最好,等等,我自己的东西,大概有20%。
如果完全讲我自己的观点,学生完全受了我个人影响,将来出去以后就麻烦了。第二,没有基础知识的介绍,你的观点也站不住脚。这一点我很受德里达启发。我在香港听过一次他的演讲,我坐在很前面,距离很近,这大概是我听英文演讲理解最多的一次。我平常听一个学者演讲,大概只能懂70%-80%,德里达的英文是第二还是第三外语,他讲得很慢,所以基本90%以上我都听懂了。对我最受启发的是什么?他开了一个课讲关于死刑,他讲的很好玩,他就说柏拉图怎么说、亚里士多德怎么说、黑格尔怎么说、海德格尔怎么说,最后留下来10%稍微讲了一下他的看法,完了。他讲话的时候也不看下面的人,我的感觉就是他跟那些人在对话,眼前那些观众好像不存在。
北青艺评:谈到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它其实是一种现代建制,现在有一些青年学者对于这个学科好像有一种虚无主义的倾向。
许子东:我知道的现状,特别在大学里面有一个讲法,现代文学这个学科可挖掘的深度有限,学科前景暗淡。我参加唐弢奖的评选时发现,现在年轻一代的学者写的论文,现代文学方面的论文侧重做资料考证,花很大的力气,比如考证出鲁迅的某一部书籍的错字,或古籍出处。相比之下,当代文学研究更多理论挑战。
当然资料考证很重要。最近看到有微博,指出我的文学课中若干材料标点有误或可增加补充。很感谢。说得不对的,也感谢。比如有人不相信老舍1966年8月23日经历的事,说太像故事。然而充满戏剧性的故事,却正是史实。
但是说现代文学整个学科没有研究前景,我不同意。为什么?我们有几百种现代文学史,首先这些文学史的生产过程就非常值得研究,因为当你建构一个现代文学叙事的时候,其实是在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当代中国的文化演变。如果认为这个学科没啥好研究,我觉得要么是你目光短浅,要么就是你非常胆怯。
第二,这个学科涵盖的作家和作品,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被超越的,还是现代中文里面最好的。就现代白话文来说,鲁迅、张爱玲、梁实秋、朱自清这些人还是最好的中文作家,怎么能说不重要呢?
“五四”一百年了,王德威有本书叫《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我的说法是,“没有五四,何来今天”。为什么?我们很客观地讲,假如中国没有“五四”,中国很可能现在仍是帝制。如果没有五四,我们设想一下,按最好的知识分子王国维、钱基博的想法发展下去,没有鲁迅胡适他们这批人,中国也可能会像日本一样君主立宪,也可能不如日本,宪法制约不了君主。所以,整个现代当代历史建立在“五四”开放的基础上。
今天大家讲不忘初心,其实还有一个初心是“五四”的初心,很简单:科学、民主、进化论。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有后来中国发生的这些变化吗?要是你享受了后来的所有成果,然后又把“五四”丢掉,觉得“五四”要么过时,要么说它错误。公平吗?
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说“五四”还不够革命;现在又有人从国学的方面,说“五四”太革命了,应该恢复国学。但我以为否定“五四”是一个危险的事。
几年前,我在香港九龙的寓所招待一些朋友,有黄子平、阎连科、刘剑梅、甘阳、陈平原等。我们一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从文”的同行,现在观点也分化了。但学者作家自觉操心民族文化发展方向,恐怕这也还是“五四”精神的遗传。
为什么要“重读鲁迅”?
北青艺评:所以您不断地在讲鲁迅,如果说“五四”是一场革命,鲁迅对这场革命的贡献最大。他的精神历程,最能体现现代中国的精神历程。
许子东:我为什么现在要做一个“重读鲁迅”的课程?读了张爱玲以后,我发现很多人迷张爱玲,我就在想,不对,我还得讲鲁迅。简单地说,整个现代文学,一是“没有五四,哪来今天”;二是现代文学里贯穿了对“进步”的反思。进步最开始是“进化论”,现在在学术界就是指“现代性”,开口闭口“现代性”,有一种对“现代性”的迷思。简单讲,“五四”以后有这样一个主流:新的比旧的好、西方比中国好、城市比乡村好,只要违反这个主流就算是反动。这些年现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对这种现代性的反思。这个现代性的反思只在学术界,远远没有推广到整体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上。当我们讲先进、进步、前进,都是自然而然的正面词,中国人传统的循环的时间观变成一个线性发展观以后产生的问题,这是现代文学当中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民族对于重大的问题都不想会怎样?
“五四”时,鲁迅他们是三面作战:一是反国学,反传统;二是反对胡适等现代评论欧美派;第三是反对后期创造社太阳社,那些年轻人脱离实际。这些论战都非常值得讨论。
“女性观”的倒退
北青艺评:除了张爱玲,其实我们今天特别值得谈的一个女作家就是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在文学史上一再地被提起,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丁玲本人也是一个“女权英雄”。我发现“五四”时期不仅是丁玲,很多男作家,鲁迅、曹禺等,都在讨论女性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他们相比其实是在退步。在很多男作家的笔下的“女性观”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五四”那个时候,很多人还试图给“娜拉”找一个出路,您怎么看这样一个变化以及女性的困境?
许子东:从现代文学的角度来谈,如果要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找一个特别代表人物的话,就是丁玲,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她与革命的关系是飞蛾扑火,到死为止;第二,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准确:丁玲最早的小说,她无意识写出了她一生的愿望,而这个愿望也是很多女性不能说的愿望,而是其深层策略。
《莎菲女士的日记》大概就是讲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故事:一个男人非常喜欢女主人公,她却喜欢另一个男人,但这个男人对她并不是真心,所以女主人公把他也抛弃了。这不只是《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故事结构,这也是丁玲一生感情道路的基本结构。丁玲的感情就是二元分化,她喜欢的男人、爱的男人,都比她高,这是她崇拜的,但得不到她也不发疯,她也有很好的伴侣留在身边。
所有男性对女性有“终极要求”,他们对付女人有三个方法:第一是把你关起来;第二个是给你好东西叫你别动,现在是给LV等;但是最有用的方法是给你植入一个芯片,一辈子只能跟一个男的好,否则就是玷污了你自己。很多女的到现在还是会这样想,这个芯片打进去以后,男人对女人的控制就非常自由,而丁玲就在这一点上反抗。张爱玲都不反抗的,张爱玲自己跟胡兰成在一起后就傻掉了,一辈子就被芯片控制,从来没好过。别人后来对她好,张爱玲晚年,赖雅和她一起生活,但她回忆的还是胡兰成,你说可怜不可怜,没办法。但是这是很真实的,张爱玲写的是很真实的。丁玲这样的女性是很少的,但丁玲的反叛最要紧,她做的第一步就是年纪轻轻就把“芯片”拿出来了。
如不能够理解丁玲对男性女性的看法,怎么可能理解丁玲?怎么解读她早期的作品?而且她作品里是无意识的,她写莎菲的时候并没有想过将来怎么生活。我们到了一定年龄就会发现,眼下做的很多事情,其实二十岁就想到了,只是你当时不知道。
“我的下一个项目会写当代文学史”
北青艺评:除了现代文学,许老师关注当下的文学创作吗?
许子东:关注,但来不及看。梁文道邀我今年参与“理想国”宝珀文学奖的评选,那个奖项就是针对当前青年的创作的,我特别喜欢上海有一个叫王占黑的作家,看了以后很感动,里面有一两篇小说看完像看孔乙己,没有故事,就是细节的谈话,写得好。总体而言,很多小说你一眼看过去,都没有什么特色,来来去去都是小资腔调,卡布奇诺咖啡馆,然后就是拍拖,把做爱写得很平淡,好像很随便,轻描淡写,真是没有王安忆他们这一代好,也许是我的偏见。
北青艺评:我特别好奇,过十年我们再来看今天的文学创作,不知道会怎么来描述?
许子东: 80年代冒出来的这批作家,占领了文坛30年,这是陈思和说的,王安忆他们统治文坛主流30年。那也没办法,而且他们的确是写得好,而且他们也努力,他们还不断变化。当然,价值观方面,就像你说的男女价值观方面,还是有些问题,尤其是主流作家。我的下一个项目会写一个当代文学史,但是大概还是要从“五四”开始讲起,一部完整的小说简史。
北青艺评:前段时间看报道,《锵锵三人行》走出演播室了,你们还去伊斯坦布尔拜访了帕慕克,你对他什么印象?这个节目现在录了多少期了?
许子东:录了好几期了,我只去了伊斯坦布尔,有和帕慕克一起对谈。文涛他们还去了希腊,详细你们看节目吧。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