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几年从70后一直到90后,似乎掀起了一股声讨原生家庭的浪潮。我们用现代的平等意识去反观自己童年时期的经历,抱怨父母的严厉、生硬、缺乏情感沟通。但是随着我们逐渐成为父母,又往往在无可奈何中,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像曾经的父母。就这样,我们所经历的,正在或多或少,或明显或隐秘地影响我们抚养孩子的方式。
本文摘编自《成为更好的父母:写给原生家庭影响下的“70末,80后” 》一书,澎湃新闻经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发布,内容聚焦于“我们还是孩子时,我们成为父母后”,我们该如何认知并接受自己的过往,以及我们该如何走出来,在自己成为父母后,不重蹈覆辙,并且做得更好。
2005—2015年, 中国迎来了第四次生育高峰。这一轮“婴儿潮”在绝对数值上并不引人注目,其特殊之处在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出生的新一代父母正式走上了育儿的前线。
2011年,我们曾讨论过普遍存在的“育儿焦虑症”。客观上,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带来了竞争焦虑,多元化社会出现的种种教育选择带来了选择焦虑,而知识信息的爆炸则使得每个教育细节都被置于放大镜下,令新一代父母无所适从。但育儿焦虑的根本,在于对成为“完美”父母的渴望。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评价说:今天的父母,“比以往任何时代的父母都更爱思考‘如何做好父母’这件事”。
如何做好父母?回答这个问题的基础在于解释另一些问题:我们如何看待童年?我们认为孩子应当拥有什么样的童年?
我们或许没有养育孩子的经历,但每个人都有关于童年的经验。在各种微信群里,谈到孩子的教育,爸爸妈妈们最常提到的一个词是“原生家庭”,最常使用的一种句式是“我小时候……”,经验的投射几乎是一种势不可当的力量。
童年在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你或许有过这样的经验:多少次,你对孩子脱口而出的话,会让你猛然想起这是小时候父母对自己说的。英国发展心理学家约翰·鲍比(John Bowlby)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孩提时与父母交往的经历使个体形成了有关自我与他人的“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这种模型将成为个性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内部工作模型的“指导”下,人们在成为父母前就已经“知道”学习其父母的角色,存在一种扮演其父母角色并重复自己儿时经历的趋势。一些实证研究显示,与儿时被父母接受或感受到父母温暖的个体相比,儿时受到父母拒绝或攻击性反应的人,在为人父母之后通常对孩子的需求和信号不敏感,不能正确理解孩子的观点,并且常会因为孩子的哭闹等焦虑信号体验到压力和威胁,从而进一步对孩子采取体罚等严厉管教行为。于是,一些抚养方式会像遗传一样呈现代际的延续。
童年对我们的另一重影响在于,我们常常会从童年的经历中去寻找解释自己的素材。这些素材可能并不完全来自记忆,也可能并不完全真实,但作为我们建构的“个人叙事”,它会指引我们的行为,勾画我们未来的方向。这些素材也构成了我们对“如何做好父母”这一问题的重要理解。我至今依然记得,年幼时,母亲如何用温柔的语调给我朗诵童话故事,我们如何一边洗澡一边背诵“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成年之后,我将自己对文字的兴趣归功于这些早年的经历,也数次期许,未来也要让自己的孩子从小体味到文学之美。
硬币的另一面是,世界上可能并不存在“完美”的童年。理想童年的拼图总有那么几块遗失。那些或多或少的童年缺憾或伤痛就像消极的回声,长久地回荡在我们心间。当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本能地决定绝不让他们拥有相同的遗憾,遭遇同样的创痛。
2016年12月28日,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条征稿启事,邀请“新一代”父母来谈谈他们的童年,以及这些童年际遇如何影响着他们今天对孩子的教育。出乎意料的是,短短10 天时间,我们就收到了超过400封来稿。并不那么出乎意料的是,这些来稿中的一些包含脉脉温情,但更普遍的是对童年,特别是对家庭生活的深深叹息。我们这批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出生的人,父母口中“最幸福的一代”,在谈到自己的童年时,却鲜有扎实的幸福感。一些人的遗憾在于父母并没有对自己的成长赋予太多的关注,另一些人则纠结于父母每时每刻的管教令人窒息,殊途同归的是,两种类型的痛点往往都在于一些未能被满足的和正确回应的情感需求。
父母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能让我们的委屈至今横亘心间。作为子女的我们为何似乎特别敏感?母亲对我回忆她的童年,总是些忆苦思甜的教育。我很小就记住了“刮锅”这个词——饭勺剐蹭着锅壁,发出尖厉的声响。童年时的母亲听到这样的声音,就知道锅里的吃食盛光了,难过得哭起来。从小到大,我从没挨过饿,受过冻。上大学的时候,每次返校,行李箱几乎要被各种食物塞爆。直到今天,回到父母身边,一顿好菜好饭仍是他们表达爱意的最重要手段。前不久我从家里回北京,父母还试图让我带一兜橙子上飞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以两个苹果成交。“有一种饿叫你妈妈觉得你饿,有一种冷叫你妈妈觉得你冷。”今天看到这句网络流行语会心一笑的人,大概都有相似的经历吧。然而,这些幸福却无法抵御内心的纠结,童年的我更渴望另外一些东西:那些被我饲养和宠爱过的动物,不要成为家里的盘中餐;考试没考好之后,父母能对我温柔一笑;在批评我之前,能否先倾听我的解释;能否多问问我:“你过得开心吗?你的烦恼是什么?”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或许能够提供一种解释。“‘70末、80后’父母一代的生活注意力更多放在对物质生活的满足上。那时候的人们可能真的觉得吃饱饭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能够生 存下来、能够生活就是幸福。他们可能受制于时代,没有办法,也没有精力去探索精神需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关梅林说,“但对下一代来讲,物质已经得到满足,他们必然会探索更高层次的需求,谁还天天为吃饱饭而高兴呢?时代背景不同,人的需要和注意力发生了变化。我们关注的东西是他们不曾关注的,也不知道如何满足的,同时也是他们匮乏的。他们没有办法回应我们,就使我们产生了匮乏感。”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提醒我,在我们成长的时代,中国社会的儿童观也在剧烈地演化。新的儿童观也会使得我们在对童年记忆的建构中产生出不同于父母一代的解读。
台湾地区学者熊秉真在《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中,谈到过去几千年中国主流儿童教育的特征:在理论体系和价值观上,有一套“成人中心”或“家长制”的设想;儿童的教育带有强烈的“功能论”和“目的至上”的特质,不但把整个人生的意义定义为做一个“有用的人”(而不是一个幸福的人,追求快乐人生、充实满意或健康活泼),更重要的是,它认为儿童的存在,是为了变成大人(当然最好是一个成功而有用的大人),至于童年阶段本身,未必有特别的意义。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儿童教育的“道德色彩”浓重,要小孩从小就学清心寡欲、省吃俭用、轻声慢动,“举止俨若成人”。
而今天,许多父母都倾向于接受“儿童中心论”,赞同苏霍姆林斯基的定位:“童年是人生最重要的时期……是真正的、灿烂的、独特的、不可重现的一种生活。”我们既希望孩子能够为成人生活做好准备,也强烈希望呵护他们的童真,不愿忽视他们作为儿童的当下的幸福体会。
儿童观的变化只是我们所经历的时代剧变的一个缩影。1970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M.米德出版了《文化与承诺——论70年代各代人之间的新关系》一书,首次对“代沟”理论做了经典而系统的分析。M.米德认为:有的文化演变十分缓慢,属于“未来重复过去”型,也称“后喻文化”,其基本特征是成年人的过去表示着新生代的未来,孩子是长者的身体和精神、土地和传统的后代;有的文化则演变得很快,属于“现在是未来的指导” 型,也称“互喻文化”,其基本特征是每一代人的行为都不同于父辈,强调青年人向同辈人学习。M.米德进一步指出:在“互喻文化”的历史阶段,社会的运行节奏明显加快,承载的信息量成倍递增,促使新一代因敏锐、活跃而崛起,新老两代人因其地位转换涉及种种观念和利益的抵触,促生出代际间的分歧和冲突。
很显然,我们对于童年的解读充满了时代冲突的烙印。孙云晓把“70末、80后”与他们父母之间的成长环境的变化称为一种“质变”,而“70末、80后”与他们的孩子相比,成长环境的变化只称得上是“量变”。“物质”与“精神”、“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一切尖锐的对立都在“70末、80后”这一代人的身上展开。我们的父母他们时代的文化养育我们,而我们却走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这些都势必让我们对自己的童年际遇产生深刻的反思,对“如何做好父母”产生不同的理解。
今天,我们追溯自己的童年,吐露那些无助、委屈和遗憾的时刻,绝不是为了把我们的父母推上审判席。事实上,无论我们多么感慨未能完满的童年带给我们的困扰,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依然知道我们童年的底色是深沉的爱,那些爱依然最能带给我们泪流满面的感动和力量。
关梅林在咨询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说‘我很爱你啊’,另一方说‘请你用我需要的方式来爱我’。”她很不赞同这样的观点:“我只要爱你,你就能够感觉到爱。我想绝大多数父母都想成为好父母,但是成为好父母是需要知识和技能的,爱的方法是需要学习的。”
我们今天追溯自己的童年,正是为了学会一种更好的表达爱的方式。这不仅仅关乎我们对下一代的爱,也关乎我们这一代人的和解。“我们对待我们的孩子可能也是一腔热血,但将来他们会如何评判我们呢?”关梅林说,“作为一个母亲,如果我的孩子未来依然觉得我做得不够,我希望他能给我一点宽容和理解。这也是我们对待我们的父母应有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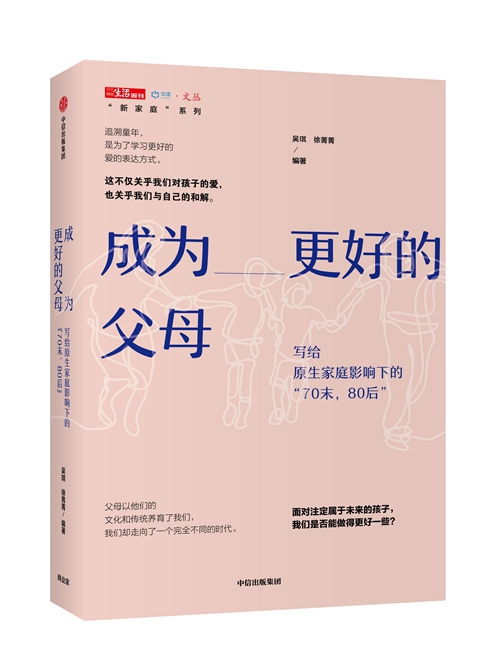
《成为更好的父母:写给原生家庭影响下的“70末,80后” 》,吴琪、徐菁菁编著,中信出版社,2019年11月。
来源:《成为更好的父母》
作者:徐菁菁
编辑:魏玮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