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珩(澎湃新闻 刘筝 绘)
1919年,经过辗转介绍,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进入紫禁城,成了为逊帝溥仪讲授英文的“洋师傅”,直到1924年溥仪出宫为止。这段为期五年的“帝师”生涯,被庄士敦写成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一书,后为掌故名家高伯雨译出,取名《紫禁城的黄昏》。2019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紫禁城的黄昏》高伯雨译注本。我们采访了谙熟晚清民国掌故的赵珩先生,请他介绍了关于庄士敦与溥仪小朝廷的种种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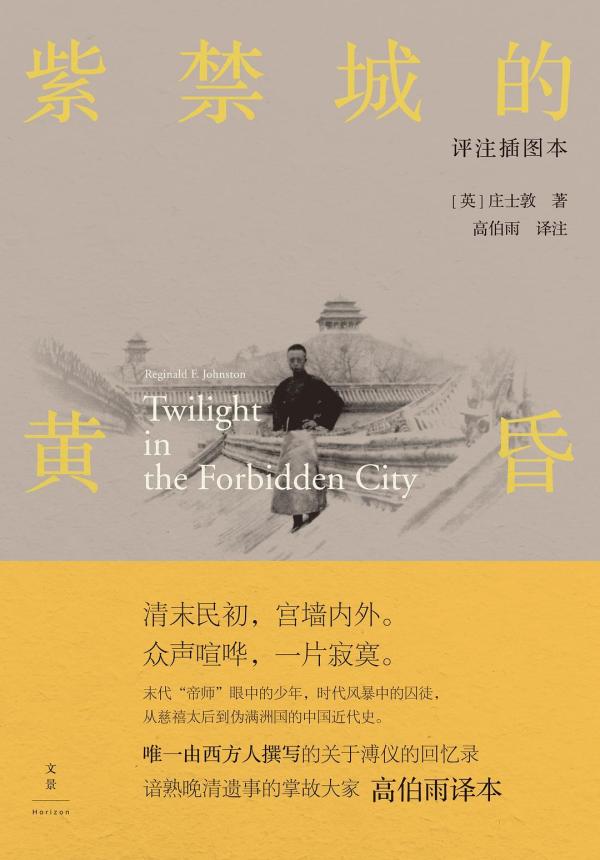
《紫禁城的黄昏》

庄士敦和溥仪
庄士敦在进宫给溥仪当帝师之前,当时的清宫是怎样的状况,能请您介绍一下吗?
赵珩:溥仪小朝廷之前的慈禧、光绪时代,还有辛亥革命,庄士敦还没到紫禁城,很多东西是说不清楚的。这个阶段的清宫情况,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实行了清室优待条件。我们今天看到的故宫太和门以内的“前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左右的文华殿和武英殿都已不再为清室所有。溥仪小朝廷的范围是南到乾清门,北到神武门,包括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这后三殿,面积虽然不小,但只剩原来的三分之一。清室优待条件在实行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说北洋与革命党的南北之争、袁世凯的洪宪称帝,以及张勋的丁巳政变。这些事情庄士敦虽然都没有经历过,对他这位“客卿”来说却是重要前奏,不然他也不会进宫。说起丁巳政变,我说一点题外话。当时是张勋带着辫子兵从徐州到北京,结果政变只维持了十二天。我在《二条十年》里提到过,我家有个男佣叫老夏,似乎曾在北洋三杰之一王士珍家里干过,后来是在我家去世的。老夏是个旗人,满脑子封建思想,给我从小灌输的东西都是张勋是好人,遗憾张勋复辟没能成功,说起丁巳政变整个过程,怎么起事,何时出发,怎么进的东华门,张勋后来如何仓皇逃到荷兰使馆避难,详细极了,就好像他亲眼看见似的。
说回正题。在这个时期,溥仪小朝廷依旧维持着原来的生活状态,用的还是宣统年号,当然,上谕、年号都不出乾清门,社会上已经是民国多少年了,乾清门以内还是宣统多少年。庄士敦也用宣统年号。所以《紫禁城的黄昏》这本书在时间标注上略有些混乱,高伯雨有的注得很清楚,有的也语焉不详。
那么,当时行走于紫禁城的都是哪些人呢?于公而言,是袁世凯、徐世昌这些人。大概1913年隆裕宾天,袁世凯、徐世昌都到场了。这是大事。隆裕的葬礼非常盛大,移出了乾清门,在太和殿举行的,而且评价也很高,匾上写着“女中尧舜”。这是袁世凯为了称帝而刻意做的准备,以示自己是有所本的。隆裕死了以后,从1912年到1924年的11月,虽然也发生过丁巳政变这种事情,但是小朝廷的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这个过程当中,溥仪慢慢长大了,到了十二三岁,就牵扯出了教育问题。行走于紫禁城的另外一些人,就是溥仪的师傅。《紫禁城的黄昏》里提到的溥仪的几位师傅,都与庄士敦有过来往,或者他比较熟悉,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也曾是帝师的陆润庠,他是苏州人,清末状元,1916年就死了,庄士敦基本没有提到。另外还有一位短暂做过帝师的袁励准,庄士敦也提得不多。袁励准出身的武进袁家跟我家关系很密切,例如袁行云、袁行霈先生都是武进袁家的子嗣。
庄士敦提到的重要人物有这么几位。首先是福建螺洲的陈宝琛,帝师领袖。其次是广东番禺的梁鼎芬,他资历不浅,但是死得较早,很早就中风了。梁鼎芬完全以遗老自居,有一张照片很有名,他去崇陵种树,表示忠于清室。还有一位朱益藩跟庄士敦接触也较多,他是江西萍乡人。最后就是伊克坦,他是满族人,教溥仪满文。不过据庄士敦说,伊克坦的满文水平究竟如何很难说,他一直一口北京话——晚清时满族人不懂满文的是多数,不像今天咱们还有满文学院、满学会。伊克坦在帝师当中最不受重视,因为溥仪对满文不大重视。
这个时候,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思潮都在涌现,庄士敦进宫是1919年,正值五四运动。如今回看起来,五四运动在文化人当中固然是有影响的,但是当时对整个社会文化产生了多大影响,这也很难说。就以京戏为例,虽然鲁迅、周作人、胡适都不怎么喜欢,但是1919年到1937年这二十年,恰恰是京戏发展最繁荣,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一个时期,贩夫走卒夜里走道,总也还哼两句“父女打渔在河下”“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这纯粹是“旧文化”。
就是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风起云涌的历史背景之中,庄士敦来到了乾清门内的紫禁城。
庄士敦是怎么得到进入紫禁城的机会的呢?
赵珩:这里面有两个关键人物。第一个是徐世昌,他负责给溥仪找师傅。徐世昌当时在北京,后来一度做了国务总理,他对清朝还是有感情的。说起来,徐世昌跟我的伯曾祖赵尔巽是有些矛盾的。我手里有一些伯曾祖和袁世凯之间的来往通信,是广东的王贵忱先生复印给我的,因为王先生专门收藏信札。从这些信札可以看出,袁世凯调解了不少我伯曾祖和徐世昌之间的矛盾,因为徐世昌在前、我伯曾祖在后,都做过东三省总督,我伯曾祖对徐世昌的很多政策并不满意,他在当地推行了很多新政——在接受新思想这一点上,他比徐世昌更开明,例如《南亭随笔》里就记载,他讲演时喜欢引用赫胥黎、华盛顿。

徐世昌
第二个是李鸿章的三子李经迈,他在威海卫做过事,徐世昌通过他辗转找到了庄士敦。据庄士敦说,本来是想找一个美国人的,但是此人要去做公使,李经迈就把自己这个苏格兰人介绍给了徐世昌。庄士敦做过殖民官员,先在香港,后在威海卫,因为反对利用宗教在中国搞渗透,很多英国人骂他。他辗转进入紫禁城之前,已经是个中国通了,游历了很多名山大川,对诗词、经学都颇有研究。当时像他这样熟悉中国、喜欢中国历史文化的外国人还有很多,比如瑞典的喜仁龙,他研究北京古建筑是一座座丈量过去的。喜仁龙那本《北京的城墙与城门》首发式由我主持,我开玩笑说,如果今天咱们想要复建一座北京城的话,这本书完全可以作为最基础的蓝图。

李经迈
对溥仪师傅这个职务,庄士敦是胜任愉快的,他觉得这对自己更深层地了解中国有好处,而且能进入这么核心的机构,也是一种荣幸。
您怎么评价《紫禁城的黄昏》的高伯雨译本?
赵珩:《紫禁城的黄昏》成书以后,一年之内就印了好几次,也有不少人将它译成中文。高伯雨这个译本是译注本,用咱们中国的经学术语来说,它不仅有注,注以外还有疏——注是注书的,疏是注注的。他的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处。一处是溥仪的生母瓜尔佳氏去世,高伯雨用将近两页篇幅的疏,详细介绍了相关背景,例如瓜尔佳氏自杀的传闻。还有一处关于延恩侯朱煜勋,这位朱煜勋一般人不大知道,高伯雨又用一大段疏对延恩侯的来龙去脉做了介绍。因为中国人历来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思想,所以延恩侯作为明代朱氏皇帝的后裔在清朝袭二等爵位,每月都有俸钱可领,但别说民国时候,就是在清末,这笔钱也常常领不下来,所以这位末代延恩侯朱煜勋是穷困潦倒。高伯雨在注之外又加了很多疏,扩大了原书的内容,这是本书很大的一个优点。
但是高伯雨的译本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高伯雨这位掌故家跟旧掌故家不太一样,第一手资料不多,他写到的很多事情,一个是道听途说,一个是翻检报刊。而且他对北京没什么感性认识。他是广东澄海人,对香港最熟悉,也在上海待过一段时间,北京的不少事物他并不熟悉。第二个问题是,高伯雨的立场是偏左的,思想比较激进,有些译文不免对庄士敦的原文有所歪曲。举个例子,书中有一处译文叫“乳臭未干的龙”,其实译成“冲龄天子”或者“襁褓中的天子”是更好的。这是典型的报人习气,按照今天的话说叫“标题党”。高伯雨的好多题目都是这种报人习气。
庄士敦和溥仪的关系怎么样?他怎么看待自己的帝师身份?
赵珩:庄士敦对中国文化、对溥仪个人的感情都是非常深的。这里面既有中国历史传统的影响,也有西洋人文精神的因素。他进宫以后,首先得找个住处,清宫花钱给他租了一处房子,在景山后街的油漆作胡同,离他的工作地点毓庆宫也近——这里历来是皇帝读书的地方。将近五年的帝师生涯之中,庄士敦是恪尽职守的。有人说他是帝国主义派来渗透的特务,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其实他并不代表政府,完全是以个人身份来做帝师,从中国人角度来说,他可以算作“客卿”。他对自己能在清宫里有这么一个差事也是以为荣幸的,他进宫时就是二品顶戴,1922年溥仪大婚又赏了头品顶戴,庄士敦是很高兴的。
前面提到,高伯雨译文中常有些对清廷不恭敬的话,这些大都不是庄士敦的原文,但是在一件事情上,高伯雨与溥仪、庄士敦立场一致,那就是对内务府的态度。因为内务府积弊已久,可以说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贪污腐化、中饱私囊。内务府管理的是宫廷事务,自然是由旗人来担任内务府总管大臣,到了溥仪小朝廷的时候,居然用了庄士敦推荐的汉人郑孝胥来总管内务府,这是有清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庄士敦一直希望整顿内务府,第一步就是遣散太监,辛亥以后太监已经裁撤了很大一部分,还剩一小部分留在神武门内,当时北府里的醇亲王载沣是不大愿意遣散太监的,但是溥仪受到庄士敦影响,决定裁撤太监,结果就是建福宫大火,溥仪猜测这是太监有意纵火,干脆把这个毒瘤彻底割了。所以,在对待内务府这个问题上应该说高伯雨与溥仪、庄士敦这三个人是一致的。我个人也觉得内务府太不像话,从前北京有句俗语:树小房新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这是嘲笑内务府官员中饱私囊,赚得盆满钵满,可是人没文化,个个都是暴发户心态,房子盖的都是新的,可是大树移不过来,挂的也都是当代名人字画。
庄士敦在溥仪身边这段时间,主要还是教皇帝学英文,跟着庄士敦几年学下来,溥仪的英文水平是不错的。另外,庄士敦教给溥仪很多新知,比如他给溥仪看了很多地图、画册,介绍各国的气候、物产,英国的君主立宪、两院制度,还有英国、法国的文学作品。庄士敦虽然在宫里当差,业余时间对中国社会还是有较多接触的,时新刊物如《新青年》他也拿去给溥仪看,虽然他并不赞同其中的思想,但还是希望溥仪能够兼收并蓄,多看点东西。溥仪当时受的教育,既有中国的旧学,也有西洋的新学,包括理科的东西——庄士敦也给溥仪讲过一点数学。我从前在《百年斯文》所收访谈(《赵珩谈襄平赵家》,《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1月5日)里也提到,我父亲赵守俨小时候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他没念过民国的小学,是在干面胡同的美国学校里长大的,与王世襄先生是同学,王先生十年一贯读了下来,我父亲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没念完。而他在家里受的是另一套教育,我祖父请了经学的老师讲左传,又请来戴绥之先生讲小学,他也是启功先生的老师。我父亲还有一个爱尔兰的老师教英文。虽然这种民间教育跟宫廷比不了,思路却是一致的——既要有旧学,又要有新知。就我所知,周一良先生、杨宪益先生都跟我父亲一样受的是这种国学、西学杂糅的教育。
在1924年北京政变以前,庄士敦其实是无意参与中国政治的,他与中国的官僚几乎没有太多接触,日常来往无非就是几位同事。陈宝琛威信很高,资历也老,庄士敦接触得最多,庄士敦在樱桃沟的别墅,陈宝琛也去过,还写了东西送给他,他都很珍视,存着一张照片。朱益藩也接触得较多。此外的几位,梁鼎芬死得较早,伊克坦教满文,跟庄士敦不搭界。在小朝廷之内行走的这五年,一些重大的活动,比如升平署的演出,庄士敦都参加了。
这个时期升平署的大规模演出只有三次。1915年敬懿太妃过生日,外面的戏班都请了进来,庄士敦没赶上。第二次规模最大,就是1922年的溥仪大婚,演了三天戏,老一点的像陈德霖,较年轻的如杨小楼、梅兰芳,这些名角儿全进宫了。第三次是1923年端康太妃过生日。
故宫的戏台很多,例如重华宫、长春宫,而升平署的演出用的是漱芳斋,它的戏台相对来说比较小,里面一个,外头一个,里面那个戏台演的是些昆曲小戏,例如《尼姑思凡》《游园惊梦》,大戏一般就在漱芳斋院子外头那个戏台。我在漱芳斋开过很多次会,里面地方很小,庄士敦看戏时场面也远不如在重华宫、颐和园看戏那么大,但也确实算件大事,所以他出席时也得穿上袍子马褂。那个时候外国使节来中国总要拜会一下逊帝,这个小朝廷的外事活动还不少,庄士敦作为帝师和客卿都会参与其中,他也觉得是种荣耀,有时候还以中国人的身份、穿着中国人的服装去接待。

穿着中式服装的庄士敦
这种好日子,基本上就过到1924年溥仪出宫。
除了您前面讲到的庄士敦的同事,庄士敦接触较多的还有哪些人?
赵珩:还有就是他的学生,例如伴读的大阿哥溥伟的儿子,后来没有了。溥仪之外,庄士敦接触最多的人就是溥杰,另外就是郭布罗·润麒,我小时候是经常跟他一块玩的,我在《二条十年》中专门有一节写到三格格金蕊秀和郭布罗·润麒。三格格那个人非常规矩、老实,郭布罗·润麒就活泼多了。他能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倒着骑自行车,说自己是马戏团的,我的印象深极了,他还跟我奶奶一块唱《四郎探母》,我奶奶演太后,他演国舅。这出戏里有大国舅和二国舅两个角色,所以人们都说戏台上这两个国舅,一个是真国舅,一个是假国舅。北京饭店的经理演的大国舅是假的,演二国舅的郭布罗·润麒是真国舅,而且他既是驸马又是国舅——驸马是因为他娶了溥仪的妹妹,国舅是因为他是婉容的弟弟。他晚年还骑摩托车,后来开了个诊所。四格格的儿媳妇跟我又是同事。我对他们都非常熟悉。
庄士敦在宫里这段时间,接触最多的无非就是这帮孩子——他是不拿溥仪当孩子的,那时溥仪已经是一个少年了,溥杰也是少年,郭布罗·润麒比他们小四五岁,还是个孩子。他们其实对各种新事物都挺感兴趣的。建福宫大火之后,原有的场地上建了个网球场,之后这帮格格阿哥就在上面打网球。溥仪为了骑自行车把宫里的门槛都锯了,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汽车也感兴趣——后来溥仪出宫,逃到天津租界的时候,他还真买了一辆汽车。
庄士敦的故居现在还在吗?
赵珩:他在城里的故居大概不在了,但是在门头沟的樱桃沟有所别墅,现在修得焕然一新。这件事跟我还有一点关系。1991年10月,我陪着剑桥大学的汉学家麦大维教授,还有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的荣新江等几位学者去了一趟。我们走的是门头沟的山路,到了樱桃沟别墅,发现根本没人管,门窗全没有了,变成了猪圈马厩。我们待了大概半个小时,麦大维教授很是伤心。我们当时就对门头沟当地热心地方文化事业的同志说,这个地方还是很有意义的,应该把它重新修缮。我回去也向文物局反映了这个问题。今天我表弟拍了张樱桃沟别墅的照片发给我,修得很好。
说到溥仪出宫,庄士敦在其中也是起到了作用的,能请您谈谈吗?
赵珩:这个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用站在逊清立场的人的说法,叫做“逼宫”。要我来形容,就是八个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是因为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倒戈一击,回师北京,吴佩孚当时不在北京,冯玉祥趁机把曹锟囚禁起来,控制了整个北京。当时社会上对溥仪小朝廷是有意见的,有人曾提出让溥仪移出紫禁城,搬到颐和园去,遭到小朝廷里的很多人反对。结果冯玉祥来硬的了,让鹿钟麟与张璧去逼宫,别说颐和园,就连乾清门内都保不住了。当时有很多遗老指着鹿钟麟的鼻子骂,你忘了先太傅了吗?因为他是晚清太傅鹿传霖的同族。鹿钟麟与张璧限定溥仪几个钟头之内出宫,什么东西都不许拿,他一点准备也没有,惊慌失措,就上北府去找醇亲王了。说到醇亲王,老醇亲王府是在鲍家街今天的中央音乐学院那个位置,后来恭王逐渐失势,醇王逐渐得势,北府是新盖的醇王府。

溥仪出宫之后,鹿钟麟(中)在清室代表绍英的带领下查看永寿宫

1961年,溥仪与鹿钟麟在北京相会
溥仪搬去了北府,庄士敦没去,依旧住在油漆作那间房子里,但是他也在多方奔走,先帮忙将溥仪移到英国使馆,后来又找了日本使馆的芳泽谦吉公使——丁巳政变,黎元洪跑到了日本使馆,丁巳政变失败,张勋跑到了荷兰使馆,使馆常常是作为避难处的。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溥仪出了一大笔钱赈灾,日本方面是非常感激溥仪的,所以芳泽公使接纳了溥仪。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当时遗老的去向基本上是四个:绝大部分人辛亥以后跑到了天津租界;有一部分人去了青岛德租界,我的伯曾祖就是这样,他对德国的印象比较好,就到青岛去了;有一部分人去了上海,像陈夔龙;还有一部分人,像善耆就去了旅顺。这四个地方都在溥仪的考虑之中,最后他去了天津。辛亥革命爆发时的湖北总兵张彪正好在天津做寓公,他不仅甘愿让出自己住的张园来接纳溥仪,还每天穿着棉袍,把棉袍的大襟藏掖在腰带里,天天来扫院子,以示对故主的忠诚。说句题外话,张彪的外孙跟我是同班同学,现在我们还经常有来往。几个月前,我去山西,专门去看了张彪的祠堂。
溥仪在天津安顿下来以后,庄士敦就离开了他,又回到威海卫。1930年威海卫交还中国,庄士敦是起了作用的。他很亲中国,所以有些英国人骂他是“英奸”、卖国贼。他回英国之后专心著述,写出了《紫禁城的黄昏》,溥仪给他写的序。成书以后,他两度到中国,第一次是1934年,第二次去了新京,那时的溥仪已经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庄士敦在书里说,溥仪其实并不甘心于做日本人的傀儡皇帝,使他下定决心离开张园去东三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孙殿英掘了他的祖坟,一时间举国哗然,对中国人而言,这是最不能忍受的。当然,溥仪身边也有很多人撺掇着他去东三省。
庄士敦的晚年很孤寂,他买了一座小岛,在小岛上插了一面龙旗,以示忠于旧主。
关于西方人对晚清宫廷生活的记述,还有《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慈禧外纪》等,庄士敦的回忆录与这些相比,有何特出之处?还有不少关于晚清生活的宫女、太监回忆录,它们与庄士敦的书相比,有什么异同吗?
赵珩:这些人的记载与庄士敦的书没有什么太多可比性。他们写的都是慈禧、光绪时代,而且带着猎奇的眼光,没有太大参考价值。再有一个,就是德龄的《御香缥缈录》。都说“德龄公主”,她其实不是公主,是慈禧认的一个干女儿,她姓裕,父亲是裕庚。德龄1942年就死了,她的妹妹容龄活到1973年,会跳芭蕾舞,中国的芭蕾舞团成立她也参与了。“文革”中,1971年的样子,我和一个同学去见容龄,她很健谈,烟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御香缥缈录》里头很多东西有错,这是难免的,人的记忆多年以后总会有偏差,每个人写东西也都有自己的立场,而且总是为尊者、亲者讳。朱家溍先生做了不少订正。
至于坊间流行的那些宫女、太监谈往录,有一本书跟我还有密切关系,那就是《老太监回忆》,后来改成《太监谈往录》。因为这本书的著作权问题,我们燕山出版社还吃官司了,我作为总编辑助理代表出版社出的庭。书的作者信修明早已不在,是他的后人把我们给告了。打死我也没想到,太监竟然还有儿子。结果人家翻出了户口本,还拿来了当地派出所开的证明。信修明确实是结婚生子了的,后来因为生活所迫才净身入宫。最后我们赔了人家五千块钱。具体到《太监谈往录》的内容,我是太熟悉了,我自己的书里还引了信修明的文章。他负责看守被烧了的圆明园,有一次接待李鸿章,他问:中堂大人是奉谕来的,还是自己来的?李鸿章说,我是自己想来看看。信修明回绝了他:您不是奉谕,不能进来。他的书里记载的都是底层的、生活化的东西。辛亥以后的溥仪小朝廷是如何生活的,溥仪这个逊帝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如何,唯一的记载是庄士敦这本《紫禁城的黄昏》,这也就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在读《紫禁城的黄昏》这本书的同时,有什么可以参照着一起读的书籍吗?
赵珩:有一本很老的书,李剑农的《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这实际上是一个简明读本,对历代内阁的情况,还有府院之争、讨袁运动、护国护法运动等,都做了介绍,就好比《纲鉴易知录》一样。另外,溥仪小朝廷之内还是有档案的,起居注的记录非常详细。当时很多人的日记、书信,对清宫之外的社会状况,以及自己偶然进宫的情况,也都有记录。这些可以与庄士敦的书合起来读。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郑诗亮
编辑:魏玮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