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中国的学术版图,从孔孟、荀韩到马融、郑玄,从韩愈、柳宗元到二程、朱熹,从李贽、王阳明到二王、戴震、康有为、梁启超等,真实生动地演绎了一代有一代之学术的历史长卷。当我们越过这一历时性视角,再从共时性维度观察扫描,则可发现,一时代之不同地域之学术,亦是异彩纷呈,气象各异。如宋朝理学的濂、洛、关、闽四个重要学派,如清代的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岭南学派、湖湘学派等。张舜徽先生明确指出:“余尝深考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高度概括出清代不同地域学派的鲜明个性和学术风格。
湖湘学派,或曰“湘学”“谭学”,又称湖南学。其称谓始于朱熹,正式定名于《宋元学案》。其源头可追溯到北宋湖南人周敦颐。至南宋,著名学者胡安国与其子胡寅、胡宏等,由福建迁往湖南衡山附近定居,开创了湖湘学派。湖湘学派经朱熹、张栻等发扬光大,泽润了一代代学人,熏陶着湖南的文化及乡风。其思想渊源、演变过程、学术成就、代表人物、师承关系、学派争论等在《张栻与湖湘学派研究》《湖湘学派源流》有完整系统的论述,相关思想“在海外新儒家那里得到了强烈的共鸣”。湖湘学派的《论语》诠释主要有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王闓运《论语训》、谢崧岱、谢崧岷《论语章数字数表》、姚绍崇《论语衍义》、聂镐敏《论语说约》等。湖湘学派《论语》诠释因其独特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形成了不拘一格、新颖卓异的独立根性。
一、不拘一格的注疏体例
中国的经学诠释,自汉代起已逾两千多年。两千多年来,经学诠释文本可谓浩如烟海,五彩缤纷的诠释文本型塑了丰富多元的诠释体例。如汉代《论语》诠释的主要文本形式是章句体和传注体。魏晋六朝时期则为“集解体”和“义疏体”。《论语》诠释史上,因时代发展、文化思潮、社会转型、主体诉求等各种因素,遂使《论语》诠释文本形式多样。或校勘,或辑佚,或全疏,或选注;通释体,专论体,笔记体,考据式,义理式,交相辉映,多彩斑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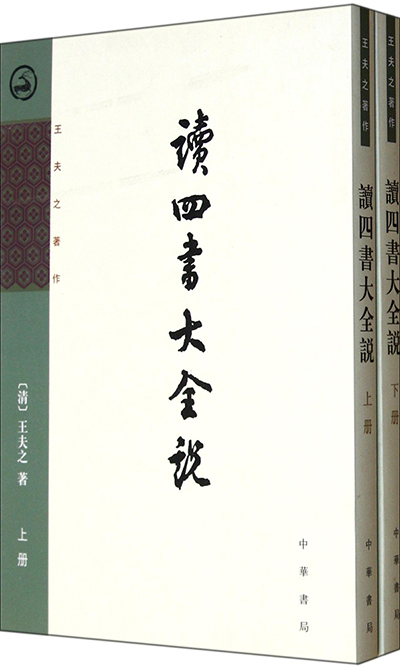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全书十卷,按《四书》原有篇章建构次序。其中说《论语》部分为卷四、卷五、卷六、卷七计四卷,每卷五篇,计二十篇。其体例大胆探索,形成如下鲜明特点:第一,每卷五篇按《论语》篇序列出篇名,按篇解说。每篇分成若干部分,不用小标题,仅以“一、二、三、四……”序数序出。如《学而篇》分成七个部分,《为政篇》为十一部分,《八佾篇》七部分。第二,王氏并非对《论语》每篇每章逐一解说,而是有感而发,自由选择。如《八佾篇》第一部分对应第4章,第二部分对应第10、11章,第三部分对应12章,第四部分对应15章,第五部分对应22章,第六部分对应23章,第七部分对应25章。第三,王氏解说时对经典原文不作具体完整的标引,只是标出关键语、词,读者通过相关语、词,细加读校勘对,才能明晓所解之篇章。如卷四第三部分通过开篇“鲜矣”“未之有也”等关键词,方可检索到此为解说《学而篇》第2章“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之内容。第四,王氏之解说或先总述此章大意,如《学而篇》第一部分开篇云:“读《论语》须是别一法在,与《学》《庸》《孟子》不同。”或转述宋儒、明儒诸说展开论说,如《为政篇》第一部分率先提出:“北辰之说,惟程氏、復心之言为精当。朱子輪藏心、射餹盘子之喻,俱不似。”可见,此书显然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胡广《四书大全》影响下的产物。其体例大胆探索,既不同于传统义疏体,又超越了宋儒之集注体,形成了王氏别具一格的读书札记体。
姚绍崇《论语衍义》,按《论语》篇目两篇一卷,共十卷。此书乃“记载老儒姚君和胡林翼讲说《论语》的笔记”,“其中文中公之说,约占二分之一”。此书之成因富有传奇色彩。姚绍崇,湖南益阳人,少年家贫,然“积学有成,尤长于《论语》”。胡文中治军鄂皖时,施以宾师之礼,邀他随营讲述《论语》。郭嵩焘序云:“文忠公治军鄂皖之交,练兵筹饷,日不暇结,而读书自课甚严,夜与桂轩会讲《论语》,亦有专程。自英山移营太湖,冒风雪行二百余里,日夕,支帐为邸舍,烧烛席地以讲。”此情此景,绝对是古今中外学术史上一段佳话。特殊的情境决定了独特的体例。全书按篇分章,分段立说,高一字列出经文,低一字演绎经义。没有音韵训诂,没有名物考据,没有旁征博引,直接解说经文大义。但为“幕府文武诸公领悟容易起见”,“好引历史上有名故事为纬以证经”。且为求通俗易懂形成独特之语体。如讲“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章,便说:“有一毫求知之心,则平时报国皆伪,如唐之仆固怀恩、李怀光,功非不奇,而卒成叛逆,则愠之为祸烈也。若汾阳王者,岂三代以下之人乎?胜国熊廷弼,才有余而度不足,日于枢臣相愤争,其决裂宜矣。”以上解说深入浅出,清晰晓畅,“使人听来兴趣盎然,潜移默化于不觉不知中”。
王闓运《论语训》共两卷,每卷各注经文十篇,采用全注形式。此体似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然文本呈现方式见其差异。第一,前者经文保持相对完整性,后者则加以拆分。如《学而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句,前者整体标引训解,而后者分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分别标引解说。第二,前者与后者之间,其经文与注文以大字、小字别之,然皇侃《义疏》经文章与章之间分行间出,给人错落之感。《论语训》依然一篇一部分,一贯到底,经文章节之间,经文注文之间,没有分行,只在经文注文之间空一字“露白”。此种略显零乱“拥挤”的体例,见出灵活率性的鲜明个性,渗透了融合汉宋的治经倾向及重视经解创新的追求。
谢崧岱、谢崧岷《论语章数字数表》二卷,卷首有光绪十三年洪良品序、十二年谢崧岱自序。其序道明是书校勘之动机。盖经书火于秦、石于汉、木于唐,在其流传过程中出现错简、衍文、增窜,引起学界诉讼纠结不止。如汉代赵岐考《孟子》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开章字计数先河。然后人不同文本与赵岐之数竟讹误孱入尤多。“由是言之,章字计数所系又非轻也,十三经字数说各不同,屡欲详核,畏难不果,尝叩名师宿儒,亦多莫知真数,前人间有标识,类多抄袭陈说,实未尝自数也。”“按经实数者,近百十年间一二人而已,虽识大者不暇识小。然已受人欺讵非儒者耻乎?考《论语》章字,版本异同,章句分合,各说不一,故宜定其所本。适逢崧岷温书,崧岱令其“校《论语》章字,汇为一表,月余乃成初稿,岱复竭半月力细为详核,除夕始就,名曰《论语章数字数表》。”是书之体例,可从《凡例》知晓:“章数以《义疏》、《正义》、《集注》三本为主,亦间采诸儒之说,然非确有证据,义理极长者,亦不敢从;问答之算一章,以问为主,答因问而有也,并问者从重,递问者并书;每章下仿《疏》例注明起止,互有多寡,各注于下,确为原有之字,后人脱漏者,据古本算入字数,原无而后人误增者亦据古本不入字数,字之异同不注。”由是观之,是书纯为考据校勘之作,便于检索,看似无聊无趣,然却“有益童蒙”。“此一役也,虽无所得,然此经字数可免受欺,又得一温书之妙法,或亦差可自娱乎?”
可见,湖湘学派《论语》诠释形式多样,体例灵活,辑佚、义理、训诂交织,全注与选注、札记与衍义融合。此与其他学派相比,特点鲜明,个性卓显。如吴派尊古崇汉,专于训诂,皖派以图释经,精于名物,显得集中单一。惟扬州学派长短交错,体例丰富,有校勘,有辑佚,有全疏,有选注,通释体,专论体,笔记体,考据式,义理式,交相辉映。然扬州学派之《论语》诠释虽不滋蔓,不拘泥,没有框框条条,没有金科玉律,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终不似湖湘学派不拘泥于简繁,不纠葛与门户,主观成分较多,铺陈色彩更浓,或有感而发,直接议论,或抓住问题,深入分析,或从哲学层面直接展开论说。
二、自由豪迈的注疏风格
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依水,典型的马蹄形地域。冬季的西伯利亚寒潮滚滚南下,长驱直入湖南全境,夏季南方的烈日加上洞庭湖的水气蒸腾而郁积不发,致使盛夏酷暑高温灼人。春秋两季时而受西北的冷锋控制,时而受西南暖色气流的影响,时晴时雨,骤冷骤热。加之毗邻贵州、两广之地,民族矛盾复杂,洪涝旱灾,饥民聚掠。独特的地域环境和文化传统,铸就了湖湘学者敦厚雄浑、不重修饰、不受拘束的淳朴活脱之性,形成了踔厉敢死、勇为天下先的士风民俗。
王夫之自幼天资聪明,4岁随长兄王介之学习,7岁完成十三经的阅读,10岁时父亲教其习读五经。王夫之极富民族气节。李自成攻克北京,夫之闻变,绝食数日。清兵南下后曾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还曾连续三次上疏弹劾东阁大学士王化澄等贪赃枉法,王化澄欲杀之,幸被义军将领所救。后隐遁衡阳石船山,筑土室曰“观生居”,潜心著述四十年,不仕清朝,“完发以终”。

王闓运画像
王闓运,少孤,为叔父教养,自幼资质驽钝但勤奋好学。《清史稿》云其“昕所习者,不成诵不食;夕所诵者,不得解不寝”,“经、史、百家,靡不诵习。笺、注、抄、校,日有定课。”9岁能文,24岁中举人,26岁赴京师应礼部会试落第。受曾国藩厚待,但只为清客不受事。应肃顺聘,甚受礼遇,然不久辞去。经邦济世理想屡遭挫折,遂绝意仕进,专事讲学著述。先后担任成都尊敬书院山长,主持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讲学授徒,弟子数千人,有门生满天下之誉。王闓运属于那种性情高旷、目无余子的人物,连曾国藩、左宗棠都不在眼里。讨厌当时官场的一切,尤其讨厌春风得意的大人物。其为人狂狷谐谑,嘻笑怒骂,讥讽嘲弄,无所不至,在近乎恶作剧的戏谑中,发泄着自己的块垒和不平。
胡林翼出身官宦之家,六岁读《论语》。“于书无所不读,然不为章句之学,笃嗜《史记》、《汉书》、《左氏传》、司马《通鉴》暨中外舆图地志,山川厄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其“少年有公子才子之目,颇豪宕不羁”。早年赈灾,既显示了踔厉风发的刚毅,又体现了尚武斗狠的悍鸷之气。治军理政,好用“霹雳”手段,获得“爱人才如命,杀坏人如麻,挥黄金如土”“三如”称号。其一生不仅表现出坚定的匡正时弊的决心、毅力和举措,也展示出极富感染的真性情,真人格,是一位个性十足极具人气备受世人瞩目的杰出历史人物。
湖湘士人独特之个性决定其注疏风格。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解《大学》《中庸》时,开篇皆有《大学序》《中庸序》,然《论语》《孟子》却没有,是疏忽,还是“不欲”,抑或“无言”?然这种“缺陷”中固然稀释了规范,当然也体现出超然率性、无可无不可的格局与胸襟。王夫之不按传统套路和体例注疏《论语》,采用抓住问题、有感而发的笔记体形式,体现出不拘一格、不落窠臼的率性洒脱品格。这种体例不仅可以对《论语》经文提出自己的见解,同时还有利于对各家之注解再作论析。王夫之爱憎分明,其诠释《论语》时屡屡对朱注提出批评,如“北辰之说,唯程氏、复心之言为精当。朱子轮藏心、射餹盘子之喻,俱不似,其云‘极似一物恒亘于中’尤为疏矣”。“《集注》未免徇曾氏太过,将‘举直错枉’作知,‘能使枉者直’作仁,便成大渗漏。”王夫之排老辟佛倾向十分鲜明。他说:“《史记》称皇帝‘生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其说出于《内经》。《内经》者,固周、秦之际精于医者之赝作耳。史氏据之以为贵,诞矣。……至云‘生而能言’,则亦佛氏‘堕地能言,唯吾独尊’之猥说也。”“……以为无思无为而天明自现,童年灵异而不待壮学,斯亦释氏夸诞之淫词。学者不察,其不乱人于禽兽也鲜矣。”“孔子既没而道裂,小儒抑为支言稗说以乱之……学者不以圣言折之,鲜不为其所欺。”“《家语》、《说苑》称子路鼓瑟,有北鄙杀伐之声,说甚猥陋。”凡怪诞虚妄之说,王夫之一概不取。
王闓运的惊世骇俗转变为经学诠释的直率放言。如王氏对《论语》较为尊崇,其《论语训序》曰:“《论语》者,盖六艺之菁华,百家之准的,其义多本于《春秋》,其言实通于上下。”然王氏尊重之余又偶出偏激言论,如“身有至德而欲人好之如色,则其言亵。”“吾不与祭如不祭,则其言拙。”“冠者五六、童子六七,同浴于沂,其言近戏。”甚至直陈《论语》存在“言悖”、“言诞”、“言歧”、“言复”、“言固”、“言陋”、“言愚”等“十蔽”。此“十蔽”无疑指向《论语》文本。这等于说《论语》根本不能称其为圣人经典,而是一叠浅薄矛盾的零散记录。让人讶异的是,王氏指出《论语》不足,然不从《论语》文本刨根问底,却将矛头对准历代经师。其曰“儒学既盛,传注益繁,汉晋分其章,宋明衍其理。皇儒考其典,经历广远,庶几备矣。然以词句易瞭,读者忽之,兼经师质实未达修辞,弟子庸下,罕知诘难,言皆如浅则思不暇详。”又云:“训诂乖互,有伤宏旨,其余疵罅,又益猥多,鲜克致疑,岂诚不惑,盖务大遗小,好博不研,缪解相传,问津无日。”显然,王氏认为《论语》经文的问题无关紧要,关键是历代经师“鲜克致疑”“罕知诘难”“好博不研”,不能作出正确的训释。足可见出自由率性、极尽牵强附会之能事。故江瀚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讥之云“其辞不逊”。王闓运的不拘个性还表现为诠释视角出人意料,他曾表明自己的治经目的只在“寻其宏旨”,用以“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训,雄文章”。其“雄文章”的理念催生其诠释语言的汪洋恣肆,颇具庄子散文风格。如训《为政》第1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其云:“北辰,燿魄宝地之全体也。众星各有轨度,地之运行四时不忒,则众星依地行而各可测,若共地而居也。”《公冶长》第7章:“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其曰:“海波汹涌,桴必败散而乘以浮海必不克济。喻以有道值无道,必见危害也。子路刚直,将不得其死。故弟子之中,惟由将从具败也。”此类语体不同于以往传统,清代毛奇龄《论语稽求篇》中偶有“插足”。其描写手法的运用,无疑增强了《论语》诠释语言的形象性。王氏时以文学手法诠释经典,虽偶受讥讽,如章炳麟说其以文学语言讲经,其学盖非为已,是为装饰穿戴,向别人显摆炫耀。此论并非空穴来风,但却丰富了诠释文本的个性。
胡林翼独特个性在《论语》诠释中亦有充分体现。《论语衍义·凡例》云:“文忠当日言及世道,便声情慷慨。以为人心不古,由于士习不醇;士习不醇,由于读书无志。如此圣经只作敲门砖用。阅时束之高阁,岂不可惜。故书中衍说时有激切语,籍以自警,体文忠之意也。”此可见出胡氏对现世人心的慨叹、对经典“旁骛”的悲哀,亦可窥见戎马仓皇中,胡林翼与姚绍崇支帐邸舍、烧烛讲经的神情风貌。胡氏慷慨激切之神态在经解中亦可窥视。其解《学而篇》第2章:文忠曰:有子言孝弟而首及于犯上作乱,此春秋将为战国之机也。春秋时礼教犹存、井田未改。乡里醇朴、必无有犯上作乱者。至于食毛践土而忍自负其生成。斩木揭竿、竟乃横行于乡邑。卒之父母为戮、同气无存。其原皆自不孝不弟始。昔王莽之末、中原鼎沸。逆党所至、杀人如麻。有蔡顺者拾桑椹供母,赤眉赠之以粮。赵礼、赵孝兄弟,遇贼争死。贼义之,得两释。人而孝弟,虽犯上作乱者,莫不起敬起爱,岂有孝弟之人而为犯上作乱之人乎……”胡氏联系史实精辟指出不孝不悌带给社会的祸乱危害,其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恍若今世。
湖湘大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孕育了湖湘学人自由豪迈的经学底色,或随意率性,或冲动不拘,在看似想当然、无章法的侃侃而谈中,展示了他们本色自然的鲜明个性和奔放盎然的生命状态。
三、质疑创新的诠释精神
湖湘文化是儒学正统文化和荆楚地域文化相激相荡的产物。儒家仁义礼智、修身齐家的目标通过荆楚山民刚烈、倔劲的个性,可以更有效地实践建树;湘人质直、刚劲的性格特质,通过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可以升华为一种人格魅力和时代精神。湖湘历代知识精英无所依傍,浩然独往,铸就了兼收并蓄、博取众长的学术品格,能够打破门户,超越藩篱,大胆质疑,包容创新。
王夫之撰《读四书大全说》就是为了质疑“异端”和“俗学”,其《论语》诠释屡屡对程朱理学提出尖锐批评,但并不狭窄偏执,而能实事求是,褒贬分明。如“唯‘严而泰、和而节’以下一段,《集注》明切可观。”“《集注》未免徇曾氏太过,将‘举直错枉’作知,‘能使枉者直’作仁,便成大渗漏。”王氏对朱子后学及其他诸儒论析具体,客观判断。如:“双峰说慎独处大错,云峰辟之为当。”“《集注》‘则心不外驰而所存自熟’,是两截语,勉斋、潜室俱作一句读下,其误不小。”“程子此段言语,想被门人记来不真,而以己意添换,遂成差谬。”“《论语》一书,先儒每有药病之说,愚尽谓不然。”王夫之在知行、道器、生死关系上,体现出辩证思维和包容理念。“凡知者或未能行,而行者则无不知。”“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特别强调行在认识中的作用。王夫之认为道总是与具体事物联系一起。“洒扫应对,形也。有形,则必有形而上者。精义入神,形而上者也。然形而上,则固有其形矣。故所言治心修身、诗书礼乐之大教,皆精义入神之形也。洒扫应对有道,精义入神有器。道为器之体,器为道之末,此本末一贯之说也。”此解源于《易》之道器说。“精义入神有器”,是说虽然入神有器,但道终为器之本。王夫之区别始终与生死:“‘始终’字,自不可作‘生死’字看。使云‘原生反死,故知死生之说’,则不待辨而自知其不可矣。所以然者,言死生则兼乎气,言始终则但言其理而已。如云气聚而生,散而死,可以聚为始而散为终乎?死生自有定期,方生之日谓之生,正死之日谓之死。但自形气言之,则初生者吾之始也,正死者吾之终也。原始反终而知死生之说,则死生所指有定,而终始所包者广矣。”王夫之兼收并蓄,在哲学高度上质疑思辨,深入分析。
王闓运《论语训》不是《集解》之翻版和摘编,其目的是“以广《集解》”,以长见闻。此种治经态度不同于陈鱣、梁廷楠,他们专取《论语》诠释之古注、古解;不同于惠栋,尊古崇汉,好古嗜博;亦不同于徐养原,重视训诂,专考鲁论。他不拘泥一端,偏寓一方。从其《论语训》所引一长串汉唐经师及文献中,既可看出其“以广《集解》”之艰辛爬梳,亦可发现其将汉代分属今古文两大阵营之经师训解杂糅一起的包容情怀。如《为政》12章,呈现包注、郑注后,舍弃郑注而选择包注,然对《八佾》第17章“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之注解,却又舍弃包注而选择郑注。当然王氏徜徉于今古之间,并非恣意猎奇,妄作采辑,而是深入分析,择善而从。充分说明王氏选择取舍时没有古今之壁垒及门户之藩篱,显示出开明多元之胸襟,具有明显的调融古今之倾向。其“教人无我,不以己所知拒人所见也”“设教不可立门户”之治经理念可窥一斑。
胡林翼出身名门,“吾宗自高祖之时,胡门乃大”。24岁中进士,授编修。年轻时代狂放不羁,目无他人。中年以后,几经挫折,在“闻道苦晚”的感叹中“折节读书”,至晚年“维德日新,几乎哲圣”,遂臻包容通脱之境界。其能将《论语》诠释自觉贯注到现实实践中,为了军政事务,为了经邦济世,能够放下个人得失恩怨,做到叩其两端,择善而从。
聂镐敏《论语说约》体现出包容古今的治经倾向。此种倾向在其另外两种著述自序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确认。《易理象数合解》自序言:“秦汉迄今,言《易》者凡二千馀家,而言理者多遗象数,言象数者多悖理,故以所得于心者,为图为解,故其书欲使《易》理与象数兼明,以矫汉人及宋儒之流弊。”《古本大学通解》自序曰:“程朱表章发明之功诚不可泯,而更改补辑,不能融洽于后人之心,亦诚有未安者。因是体会贯解,以复古人之旧观,识经传之定界。”由此,足可清晰窥出其贯通古今、兼采汉宋之学术路向。
湖湘学派包容豁达之胸襟,无适莫心、无人己见的无可无不可之境界,有助于转益多师,激荡迸发,能够打破常规,超越前贤,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创新突破。
胡林翼敢为人先。其云:“天下事只在人力作为,到水尽山穷之时,自有路走,只要切实去办。”胡林翼创新了演义体,在军营中讲解诠释论语,且结合史传现实阐述论语,开启了崭新的诠释方式,拓展了经典的时空疆域,极大地提升了《论语》与现实的关联。
王夫之《论语》诠释分析深邃,见解独特。《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书析理极精。于《大全》所引朱子之说,有绝非出自朱子而为门人所假托者;有虽为朱子之说而专诂某章、不可移之他章者;有的为朱子之说,而亦不可从者;有意甚是而说不详者,而诸儒之说,又互有是非。皆一一为剖辨之,驳正之,引申之。至于释氏狂谬,解姚江偏见。分别尤严,曲尽洞达。词畅而理无不显。不徒为大全诤友也。”此书论世臣,议旧制,“则察于古今治乱之故。卓识宏议。非复经生所能道矣……”如其论及人与兽的区别时云:“若人之并与禽兽者,则自性而形,自道而器,极乎广大,近乎精微,莫非异者,则可以仁义二字括之。”“性之并者,人道也;形之异者,天道也。”此在《思问录内篇》中阐述得更加透彻精辟,“天道不遗于禽兽,而人道则为人之独”。在王夫之的世界里,人与禽兽的根本标志在仁义道德,全盘否定了朱熹所谓财狼、蜂蚁皆有仁义忠孝的无稽之谈,尽显王氏大胆质疑、勇于突破的创新精神。
王闓运勇于怀疑,著《论语训》就是为了和历代经师“叫板”。斥其“未达修辞”、“罕知诘难”、“质实”、“庸下”、“言浅”。其敢为人先的背后,多少有点轻率,以至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说他“经学所造甚浅”。田汉云先生在《近代经学史》中,从三个方面考其解经之“浅”,即“词句训释之浅”、“义理阐释之浅”、“援据经典以切当世政治方面无所发明”。平心而论,就《论语》研究而言,王氏显然没有俞樾深入精湛,也没有焦循广博深邃。但若对其文本深入细读,尚可发现王氏之有关训解尚有一定新意。如《宪问》第1章原宪问:“克伐怨欲不行,可以为仁矣?”孔子说:“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王氏解曰:“未能本于礼。不克伐怨,不忮也;不欲,不求也。但自守而已。非克己复礼之仁。”关于此章之解释,历代经师多从个人操守方面言说孔子云“难矣”及“不知”之原因。何晏《集解》、皇侃《义疏》、邢昺《注疏》未作具体解释。程子之解虽有一定深度,但仍未超越个人品行之窠臼。王氏另辟一途,强调为仁、达仁,当从礼始,仁本于礼。不行克伐怨欲,仅是自守而已,未能称仁,或不是“克己复礼”之仁。欲求仁成仁,不仅要不行克伐怨欲,还要在礼上扎实下一番功夫,以礼为本,以礼节之,以礼行之,以礼立之,方可“为仁”,方能实现“克己复礼”之仁。王氏此解打破以往之定势,显得新颖独特,给人启发。
又如《颜渊》第8章“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句,历代之经解,纷纭复杂,或失之于牵强,或失之于模糊。皇侃、邢昺似均有重文之偏向,仿佛去“文”则物之无别。且君子小人之别亦仅在于其“文”,君子小人其“质”之区别无关紧要。朱熹显然不满,其解无疑有反拨纠谬之功,但未作深解,不够具体透彻。刘宝楠虽将虎豹犬羊文质之移植优化,虽然富有创意,但过于牵强,仅是调融折中而已,显得笼统概括。王氏云:“虎犬生则质异,死则以文贵。使犬有虎文必贵犬矣。贵犬则虽质不如虎,而虎亦不见贵。盖重文者人情也。故貂貉贵于虎豹,然则质反附文而行。”王氏强调了虎豹犬羊其质天生有别,尽管使犬有虎文,则此犬必贵,然此犬之质仍不如虎。此突出了虎豹有虎豹之文质,犬羊有犬羊之文质。不同事物、不同对象有不同的文质之关联,就如同审美类文章之文质不同于应用类文章之文质一样,文质紧密相连,不可剥离。然文质之关联并非一成不变,虎豹犬羊死则以文贵。且倘使犬有虎文则此犬必贵,尽管此犬其质不如虎,然虎却不见贵。即文变而质未变,质未变却又为何产生贵贱之变?为什么?是人为的因素,是人们的认识、判断、观念,决定了客观事物的性质和价值。王氏指出:“盖重文者人情也。故貂貉贵于虎豹,然则质反附文而行。”王氏此解虽有附会臆测之嫌,但他从社会生活、价值观念角度,独辟新径,揭示了“文质”之异化现象,启发人们向经义深度、广度掘进。如此之独特视角,如此之卓异之见,无疑拓展了《论语》的诠释空间。
四、安邦利民的淑世情怀
古代湖南偏隅西南,道路崎岖,交通不便,加之多民族杂聚,故在文化上受中原文化浸染较少,“与江浙士大夫隔绝”,且深厚的经世传统亦让逐渐盛行的考据学“没能得以风靡湖南”,致使“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经世之志”。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安国、胡宏十分重视治术的作用,其研究《春秋》经传,就是要从中挖掘出安世济民的良药。崇尚实学的学风,先忧后乐的爱国传统,投身政治的献身精神,构成了湖湖人文群体的心理结构。由此,湖南学派淑世情怀似乎是自然环境与儒学传统的氤氲缭绕、耦合升华。
王夫之《论语》诠释之独特体例就是提倡实学、讲究效率的探索示范。他反对“但取经中片句只字与彼相似者以为文过之媒”,而对详略相因、一以贯之、为天德王道之全书大义,却“茫然置之而不恤”。王夫之对空疏之学的批判,扬起了清初实学思潮的风帆。王氏尽废古今虚渺之说,高举经世致用大旗,激活了传统儒学修齐治平的经世精神。其解《颜渊篇》“颜渊问仁”章云:“‘天下归仁’,须日日常恁地见德于天下,岂一归之而永终誉乎?如孔子相鲁时,天下归其政之仁;及其政删修,天下又归其教之仁;何曾把一件大功名盖覆一生去?‘天下归仁’非一日之小效,‘克己复礼’又何一日之成功耶?自‘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之前,到此一日,则有维新气象,物我同之。”此强调“天下归仁”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不可速战速决,需要不断改革维新。此将天下归仁落实在社会发展进步层面,其经世特征清晰突出。其解《卫灵公篇》“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章强调:“无为”不是“不为”,“有为”不是“必欲为”。“无为”“有为”,皆欲因势利导,与时俱进,其“创作”“改制”皆要有利“民用”,以显“治著”,“以集其成”,其本质依然落实在致用层面。
王闓运诠释《论语》,经世致用之倾向十分鲜明。其解《卫灵公》31章“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季氏解曰:“今古阻绝,典籍无考,故劳于思”,“事非思所能知,则道非思所可适也”,“即今所传经而学之,通经必能致用矣”,直接指出徒思不能致知,不可适道,“通经必能致用”。王氏之经世思想,在其对孔子弟子的评价上昭示得格外清晰。如解《宪问》第17章,涉及管仲评价时云:“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当死。”强调指出:“仁人以及物为功,立君亦以为民也。苟利于民愈于仗节死义者。”此从“及物”、“利民”角度褒扬管仲,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色彩。又如,解《先进》19章 “赐不受命”时,自下断语曰:“言赐颖悟不待教也。”其拔高乃至神化子贡之情感不言而喻。解“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时,自作判断:“货殖谓多学而识,如人之积货也。亿盈也,积学既盈,亦能中道,回虚而赐实也。”王氏指出“回虚而赐实”,显然打破了《汉书货殖传》云孔子“贤颜渊而讥子贡”的评价范式,认同“赐实”,实际是对子贡热中于经商的肯定,无疑渗透了经世之实学情怀。
胡林翼出身翰林, 自幼受湖湘经世文化的陶冶。其父胡达源讲学城南书院,“祖汉称宋”,教人“务实学”。胡林翼在求学过程中,所从之师多为经世致用派人物,贺熙龄、蔡用锡、陶澎、林则徐对他影响最大。遂萌发经世改良思想,“不为章句之学,笃嗜《史记》、《汉书》、《左传》、司马《通鉴》及中外舆图、地志、山川随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胡林翼在政治实践中,将理学中的哲学、儒学思想广泛应用于吏治、军事、经济、人才等各个实践方面,认为吏治、兵事、理才乃儒学致用之精髓。其与姚绍崇讨论《论语》时,大多联系历史和当时政治军事之论。阐述其经世致用思想。如解释《学而篇》“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时强调交友贵诚,方可立功。在他们眼里,立诚交友,建功立业,远比“学问”重要。一旦立功,则“何俟他求”?其实学思想昭然若揭。这种倾向在解释《先进篇》“公西华侍坐”章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其曰:“观唐自肃代,专行姑息,骄兵悍卒,辄逐主帅。至于五代,天子亦惟所推戴。故夫外交军旅内仍水旱,率饥罢之众,以战则溃,以守则乱,不知方故也。士能知方,虽一成一旅,而可以立国。”士能知方,可以备战治乱,富强立国。否则将战争频仍,天下大乱。胡氏又云:“且民者君之身也,会计之臣,专务足君,不务足民。唐太宗有言:剥民以奉君,譬如馋人自啖其肉,肉尽则身死。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悉索敝赋几,如北汉刘崇民不胜诛。求之苦而能有以足之,则地虽小而根本不僵。五代杨邠常言:国家府库实甲兵强乃为急务,至于文章礼乐,何足介意。鲁至定哀,中原多故,衣裳之会熄矣。然夹谷一相,齐不敢轻鲁,故干戈俎豆并习,而后为国有人焉。若此者,民皆忠信,甲胄不在外而在心。户庆仓箱粮储不在上而在下,卒有事变举而措之裕如也。”此处再次突出民足君足,国泰民富,国强兵强,乃为急务,而“文章礼乐”,何足介意?此解虽有偏颇,但在一定时期却也精准深刻,突出体现湖湘学派经邦济世之伟岸情怀。
五、小结
湖湘大地,“深山大泽,实产龙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锻炼了湖湘士民百折不挠、坚强勇毅的性格和独立思考、浩然独往的自由精神。湖湘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从屈原到张栻,从王船山到魏源,从谭嗣同到蔡锷、毛泽东,流淌着激情和理性,激荡着对天道人伦、思想文化、民族国家的思考探索、自强奋进。
湖湘文化独立根性的哲学依据源于《周易》“天行健”之宇宙精神,此为湖湘文化自强不息的“人极”范畴。其孕育了湖湘学人“独立不羁,遁世不闷”的特殊品格、“舍我其谁”“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气概,塑造了湖湘学者在深谙古学的同时又能“独辟蹊径”的自由独立之思想,“救中国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的殉道气慨。湖湘学派的独立根性积淀为湖湘士民敢于冲决网罗的文化底蕴,演化出强烈的求新求变精神,汇聚成中国近代社会学术转型和民族救亡的重要思想资源。
迄今,学界关于湖湘学派之“独立根性”论述颇多。杨毓麟认为是“湘人无奴性”,冯友兰描述为“楚人之精神”,鲁迅称之为“楚人的蛮性”,钱基博则强调湘人能自创风气,并能别于中原人物而独立。湖湘学派之独立根性在宋代以前无所表现,宋代以后才逐渐“自振于他省之外”,且在哲学、史学、经学、政治乃至西学等领域蔚成风气。这种特点只有经过社会实践的长期熏陶和悠远文化的历史积淀,才能在各种不同的情境和各种不同的活动中表现出稳定的心理特征和鲜明的情感倾向。
湖湘学派《论语》诠释的独特个性绽放为不守成法,没有藩篱,大胆怀疑,勇于创新,生动展示了湖湘学者灵活率性的生动个性和自由豪迈的盎然意气,为《论语》诠释画廊增添了鲜活的色彩,在《论语》诠释史上放射出独特的光芒。湖湘学派高举公羊学变法大旗、倡导安邦利民的经世致用思想,对推动中国文化与历史之进程功莫大焉,对探索传统文化活化创新、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具有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
本文节选自《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柳宏、宋展云/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版),略作删改。

来源:《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
作者:柳宏
编辑:魏玮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