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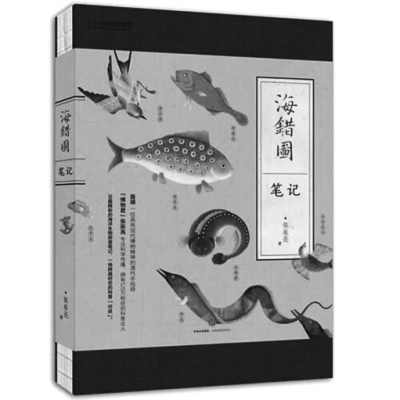
上海、杭州、北京……被称为“科学网红”的张辰亮,带着他的新书《海错图笔记》转了一圈,年初回到了北京。各地的读者见面会上,都能看到他为读者妙趣横生地鉴定、解读古书中的海洋生物。台下的读者有老有少,却因为对大自然的热爱而聚在一起。张辰亮则一副波澜不惊的沉着样,面无表情,话语却暗藏包袱,不时引得读者捧腹大笑。
见到张辰亮那天,窗外的寒风仍在楼宇间呼啸,而他家的客厅内,满眼葱郁的绿植,正和他一起享受午后的暖阳。似能意会绿植心事的张辰亮在我来到前已泡好红茶,精心备下了茶杯和他的博物故事。
爱养虫子的好奇少年
张辰亮是北京孩子,从小生活在大屯。那时候家附近有工厂,周围大多是五六层的宿舍板楼,灰墙灰瓦的,没什么看头。
他最喜欢去姥姥家玩儿。为什么?因为姥姥家门口唱大戏呀!
原来姥姥家在十里堡,那里有火车道、菜地、河沟、芦苇。随便一个地方就是天然的舞台。这出戏没有导演,纯粹是大自然的安排,连演员也是即兴表演。他翻开砖头,看到一只被“拍死”的蜘蛛,伸手一碰它却跑了,行动极快;他在这里看到了蝴蝶蛹,满心欢喜地等待蝴蝶飞出,却最终发现近100多只蜂的小幼虫死在里面。
这个自然的世界简单又神奇,在张辰亮心里不断闪耀着光芒。
张辰亮的母亲是学校的数学老师,所以很早就发现了孩子乐于观察的爱好,并鼓励他自己寻找答案。学校的图书馆也让他从更多角度了解这个简单又神奇的自然界。
“有一次雨后,我看蜻蜓在水坑里款款飞旋,不时将细长的尾巴弯成弓状点进水草丛中,水面因此扩开一圈圈波纹。我就很想知道蜻蜓在做什么。”在图书馆翻开昆虫的少儿读物才知道,蜻蜓点水就是在产卵,卵直接产入水中或水草上。卵孵化出来的稚虫即水虿,它常伸出勾状带爪钩的下唇,捕捉水中的蝌蚪为生。
这是从大人口中不一定能得到的知识。“所以小时候的图书馆就满足了我对世界的大部分好奇。”这个世界一旦敞开,张辰亮就看到了表面之下隐藏的众多有趣,它们成为他紧张学习之外的调剂。
很多成年人都记得小时候常在大树上爬着的手指大小的绿虫子,肉肉的,还有着小爪子。男生经常抓起来,用来吓唬女生。张辰亮也抓过——为了写观察笔记。
“我知道那是天蛾的幼虫,平时在树上,掉在地上后会钻进土里化蛹,最后成为天蛾飞走。每个阶段它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我到现在为止就见过一次那么美丽的蜕变。”一天,张辰亮逮住了一只幼虫,在鱼缸里铺上土,幼虫自然就钻了进去。
等再次打开时,眼前的场景让张辰亮着实震惊了一番:幼虫的头部是红色的,身体是绿色的,透明如翡翠,尾部则呈现为褐色。“那就是天蛾幼虫正在化蛹的过程。尾部已经完全蜕变,身体正在蜕变,头部还未发生变化。不同的幼虫颜色会不一样,但大概的生长模式都是一样的。”
从那之后,家中角落里开始慢慢出现小昆虫的幼虫:磁带盒里、鱼缸里、阳台上,瓢虫的卵、螳螂的卵、趴在叶子上的蚜虫……在很短的时间内,各种小昆虫完成了生长的过程,被张辰亮细细观察之后,写入日记,并最终放飞。
“但小时候还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都是杂乱地知道些小知识,没有形成体系。”
随着观察和了解的深入,表面上的知识显然不能满足这个成绩优秀学生的好奇心。
上高中时,张辰亮找来了大学的普通昆虫学教材,并在网上找到了“中国昆虫爱好者”和“大自然社区”两个论坛。从潜水开始,慢慢地和专业的硕士博士交流,也从他们那里知道了更专业的知识来源。
“我之前看的书多是日本学者写、台湾学者翻译、大陆出版。这就存在知识水土不服的问题,比如研究方法,比如命名规则。”有一天,学者们在论坛里讨论锹甲——一种雄性长大长牙、夹人特别疼的昆虫。看过照片之后,张辰亮疑惑不解:这不是锹形虫吗?为什么叫锹甲呢?
网友回复他,锹甲是大陆的叫法。大陆的学者通常以命名规则来体现昆虫的科属目等特性。例如锹甲等名字中带“甲”的昆虫,都是鞘翅目的,身体外部有硬壳,前翅是角质,厚且硬,后翅是膜质。“想要了解中国的昆虫学,就要使用中国的昆虫学语言,才能和大家进行沟通。”
为科学打广告的博物小亮
大年三十晚上,网友贴出了一张自家柠檬树的照片,叶子上有着薄厚不均的泥土,同时在微博上喊话《博物》杂志:我家的柠檬树怎么了?
《博物》杂志的官方微博在回复中写道:“你不给它洗澡,太脏了,脏得出包浆了,包浆变成皮壳,最后皮壳都裂开了,树说我可算喘口气儿了。”
《博物》是《中国国家地理》的子刊,被称为《中国国家地理》的青春版,主要的阅读人群就是学生。这个官方微博的管理者就是张辰亮,“博物君”则是网友们对杂志官方微博的昵称。
张辰亮曾经也是《博物》杂志的忠实读者,在2004年上高二时还被评选为博物少年进行报道。如今作为这个杂志官微的管理员,他每天与网友保持着将近2000条的互动,用他的话说,这是为科学打广告。
看起来轻松,但当时决定做科普时,也有些无奈。2006年,刚上大一的张辰亮就创办了南京农业大学昆虫协会,与志同道合的同学共同切磋。在中国农业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时,他选择了研究半翅目昆虫,并专注于臭屁虫的研究。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张辰亮发现科研变成了每天做研究、看英文文献、用大众看不懂的一套语言去写学术论文。“就我而言,我不希望把一个本来的爱好变得枯燥,所以就选择了科普。”
2011年,研究生在读的张辰亮来到《博物》编辑部实习,接手的第一项任务便是运营当时仅仅2万粉丝的官方微博。“我当时还在实习,就把这么重要的任务给我了,所以我很用心。”张辰亮说。
为了增加微博的亲和力,张辰亮一改官微谨小慎微、一脸严肃的面孔,增加内容的趣味性,努力“卖萌”。可慢慢的,无话不萌,让人读了不断起鸡皮疙瘩。“我觉得官方微博能够吸引粉丝,应该在于真实。卖萌只是一个人的一个侧面,就像我喜欢昆虫,也只是我的一个侧面。一个人不可能每天每一句话都在卖萌,虚假的‘亲切’再亲,最终还是会被人嫌弃。”
一筹莫展之际,编辑部交代给了这个实习生新的任务:尝试回答网友发来的提问。跳出窠臼,张辰亮有了明确的方向,开始充当起网友的生活百科全书,解答各类问题。同时,张辰亮开始注重将官微人格化、立体化,“我想让它有感情,不让人觉得是在装。哪怕是幽默,也只能是一个侧面。”于是,张辰亮又多了个高冷的科普男神的称号。
“博物君,这是什么蛇?有毒吗?”照片里是盘作一团的褐色条状物,评论里一堆惊恐的吱哇乱叫。
——博物君答:“绳子。”
一只灰色大鸟在防盗窗上筑巢,“博物君,这是什么鸟?我该怎么做?”
——博物君答:“珠颈斑鸠,爱在人类窗台上孵蛋。你什么都不用做,趁它外出时把那半倒不倒的花盆扶正了就行,我看着难受。”
在不断的互动中,张辰亮加入了北京男孩特有的大胆:可能是冒犯,可能是讽刺,也有可能是揭短,但他们都是出于一个普通人的真实表现。这样一个立体而有性格的官微慢慢得到了广大网友的认同和接受。
网友们对张辰亮的喜爱溢于言表,经常拿他开玩笑,他则一概接受。每天《博物》杂志的微博都会跳出几千个新提问。千奇百怪的动植物照片、“来不及拍照”的手画生物,还有“梦里见过的怪兽”,地摊里的真假古董,匾额上的甲骨文……几千个@“滴滴”叫着,等博物君一一投喂。
每天他还会挑选几条提问转发,粉丝们戏称为“被翻牌”。这些“被翻牌”的微博,或因物种奇特,或因回答机智,平均五条就有一条点赞破万。张辰亮的“翻牌”标准是:“首先这个东西得很好玩,或者我能答得很好玩。其次要有代表性,也是他们想问的,所以转出来大家一看。”
一路欢笑高歌,《博物》杂志的粉丝量从最初接手时的2万,如今已超610万。那个沉默羞涩的年轻人,也娶了妻生了女儿,但内心世界并没有什么变化。这个由昆虫而起的乐趣,只是从一人独享变成了众人共享。
破案《海错图》
“水母以虾为目,有人要捞它的时候,虾就提醒它沉下去。但我一直没见过,直到有一次网友发来照片,我一看还真是!然后就把这张照片放进我的《海错图笔记》里了。”张辰亮手中拿着的《海错图》几乎被小纸条贴满,很轻易就可以在《海错图笔记》中找到对应的章节。
从昆虫到海洋生物,看似相隔甚远,实则在一个圈里。张辰亮说,除了专门从事研究外,只有新入门的人会单独地在一个领域。“这个圈子其实都是相通的,你要想养昆虫,就得知道它吃什么草,有没有可替代的草料,它生长在什么环境,它的天敌是什么等等。”一个个圈子触类旁通,就融合在了一起。
从小时候起,每去海边旅游时,张辰亮都直奔沙滩最边缘的礁石区。“礁石区的生物密度远大于陆地,海洋的生物密度比礁石区还大。所以翻开礁石,眼前的场景都会让我很兴奋:石头上附着藤壶、海藻,石缝里藏着小螃蟹,积满海水的石窝里满是伸开触手的海葵、傻头傻脑的小鱼、背着螺壳的寄居蟹……”即便是结婚后去泰国旅游,妻子逛街购物时,张辰亮也会趁机溜到海边浮潜,观察水下生物。
张辰亮入职《博物》杂志后,经常负责专题的稿件撰写。那些积攒下来的笔记就派上了用场。“我去各地出差都会去菜市场看看,有时候为了专门看一种水产,早上五六点就要去,因为有些水产是饲料,去晚了就被拿去喂食了。”
一点点积累下来,就成了《海错图笔记》。《海错图》的作者叫聂璜,出生于明末的杭州,是一位画家兼生物爱好者。康熙年间,聂璜游历了河北、天津、浙江、福建的很多沿海地区,考察海洋生物,每看到或听说一种生物,就把它画下来,之后再翻阅书籍进行考证,并采访当地渔民来验证真伪。书成后一直流于民间。雍正四年,这一年的皇宫档案记载,太监苏培盛把《海错图》带入了宫中。后在故宫文物南迁中,全套四册书分了家。现在前三册《海错图》留在了北京故宫,第四册则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海错图》一开始就没打算给皇家欣赏,所以与同时期的其他画作风格完全不一样。”张辰亮说,正是这种与众不同,让他初见《海错图》就被迷住了。
十几年前,还在上中学的张辰亮去故宫玩,在书画展区的一排动物画谱前观察了许久,“就快扎进去翻了。沿着展台看过去,第一本是《鸟谱》,里面是精美绝伦的花鸟画;第二本是《鹁鸽谱》,各种古代观赏鸽;第三本《兽谱》则画了各种走兽,里面有一张是一头黑猪。当时我觉得有点好笑,一头猪也值得画进皇家画谱?”
再往前走,张辰亮被眼前这奇怪的画风吸引了。“看到最后一本《海错图》时,那头猪已经完全不算什么了。画谱里全是稀奇古怪的海洋生物。动物的神态十分卡通,可又一本正经的学究样子,不能说是工笔画,更不能说是漫画。这些动物好像在现实中也都有原型,比如有一幅说是‘井鱼’,画了一只头顶喷水的大海兽,一看就知道原型是鲸鱼。”
上学时只能阅读书籍,工作后要为杂志撰写和策划海鲜类稿件,张辰亮有了去各地沿海探访、在珊瑚礁海域浮潜、拍摄海洋生物的机会,年少时产生的对《海错图》的兴趣却一直未减。2014年,《海错图》被故宫出版了,张辰亮立马跑到神武门旁的售卖点买了一本。
“错是种类繁多错杂的意思,汉代以前,人们就用‘海错’来指代各种海洋生物。当天我就看完了这本书,不愧是海错图!”张辰亮介绍,《海错图》很有现代博物学风格,每种生物所配的文字,既有观察记录,又有文献考证,并配趣味“小赞”一首,读来令人兴致盎然。
但张辰亮也对书中的内容有所保留。“因为有些动物聂璜并非亲眼所见,而是根据别人描述绘制,外形和生物习性的记载也就真假混杂了。”但这些质疑也促成了他进行考证:“我可以从文字和画中发现蛛丝马迹,辨别真伪,然后推理分析,鉴定出画中生物的真身。这就像破案一样,非常过瘾。”
一如说这话时的条理清晰,张辰亮从2015年夏天开始将关于海洋生物的探索进行合并,专门从今天的生物学的角度,对《海错图》中的生物进行分析、考证。在这期间,除了翻阅各种资料,他还去过辽宁、福建、广东、广西、天津以及日本、泰国等地实地考证。一年半过去了,不知不觉也写了30篇文章。“我就先把手头有的东西集成册,让大家看着玩儿。看完后,如果读者觉得这是一本有意思的书,那我就很高兴了。”
不问有用吗,只为我喜欢
几天前,张辰亮刚刚收获了他高颜值的“小棉袄”,升级为父亲,由此开启了人生新的阶段,不免思绪良多。
“11年前大学新生报到,我们一个班30多人一多半是调剂过来的,一些同学对昆虫学一无所知,而且男少女多,大多对昆虫不感兴趣。”张辰亮则按照老师的要求捕虫子、做标本、写观察笔记,因而他的书本成了期末考试时的抢手货,同学们考试通过也多需要找他帮忙辨认昆虫。
毕业后,大学同学天南海北,各自成家立业,仅有很少一部分从事植物保护或昆虫专业的科研和科普。“我现在想,当时的植物保护以及昆虫学其实还未被大家认同。比如学金融、学法律,都知道毕业后干什么,但我这个专业回答不了。”
昆虫种类占自然界中生物种类的五分之四以上,远远超过植物和微生物。可以说,没有了昆虫,就没有了大自然的生物多样性。因而在欧美国家,喜欢昆虫是一个很高雅的爱好,荷兰、美国甚至还举办过昆虫节。
“对我来说,昆虫也好,海洋生物也罢,我知道这些,不是因为它有用,就是因为喜欢。”因为喜欢,张辰亮才不断了解这些有趣的知识,并传播给大家,解决大家的困惑。“之所以被问到‘有什么用’,是因为喜欢昆虫或者博物的人还没有那么多,还是一个小世界的爱好。但这个世界又格外简单,只需要观察和了解就好,纯粹是知识层面的探讨,远离了世俗纷扰。因为压根它就是个兴趣,不是以有用为目的呈现的。”
小时候,张辰亮在树上逮了一只很漂亮的蝉,他问身边的父母、老师,又查书,却怎么也找不到答案,后来在论坛里,才知道它叫斑衣蜡蝉。“我现在就扮演了那个回答问题者的角色,成为大家的博物君。”
张辰亮的生活因此很简单,面对网上的提问尽力回答,不懂的去查找资料,但如果有人不怀好意地攻击,他也不会陷入骂战之中。“其实有610万粉丝这件事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很好地交流,但另一方面有时候也很难驾驭。”
数日前,张辰亮接到了一封来信,对方是南方一座小城的高三学生,他俩有着同样的爱好,想要报考北大生命科学的相关专业。但学生问:“这是不是不务正业?”
“我现在做的科学传播,就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我的存在对别人是有意义的,我不觉得这个爱好是不务正业。”张辰亮说,这既是给学生的回信,也是给即将而立的自己的一个交代。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