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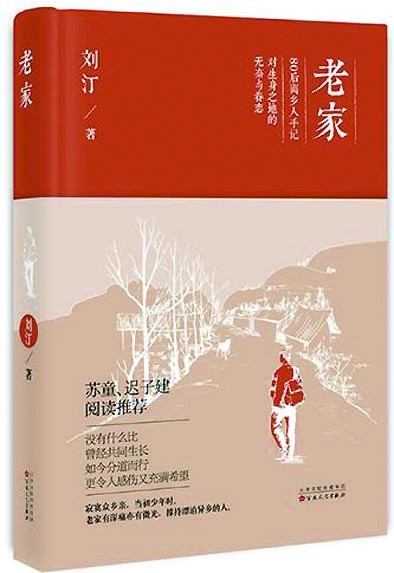
散文集《老家》近日出版
离开老家的日子里,刘汀想起最多的场景,是农民,特别是他的族人劳作的场景,在远离北京的内蒙古自治区海力图村富河屯,人们耕种、拔草、收割、晾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深深地记得年少时在田中“点豆子”的情景:耕种的时候,祖父或父亲赶着牛在前面犁地,母亲在撒麦种或谷种,而他磕磕绊绊地隔三五步在垄沟里点上几颗豆子,身后的叔父把土肥撒进田里……那些曾参与的劳作,尽管经历时光蹉跎,却依然在生命中留下深刻印记。
这样的场景太多了,它们构成了“老家”的基本景观。与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如今的刘汀只能在千里之外的城市里,看着万千灯火,偶尔回想老家那微茫的星空和春日的播种,然后,在微博上给自己取一个“刘村长”的名号。与其他离乡人不一样的是,刘汀是个“写字的人”。文学是他生活的方法论,或者说,他以文学为方法论来思考、面对世界和自我。当年这个在旁人看似不“经济”、不“顺应潮流”的选择,如今却带给了他回忆、观察和书写的便利。近日,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他的散文集《老家》,这部“80后”离乡人手记,写出了他对生身之地的眷恋与无奈,蕴藉困苦与暖甜的老家,“曾经共同生长,如今分道而行”。老家有深痛亦有微光,撑持漂泊异乡的人。
《老家》说的是老家的人,老家的事,老家的景,老家的情。“这些老家人物的悲欢离合与命运变迁,在刘汀笔下不只是单个儿的画像,而是悄然折射出了时代的变迁——假如这部小书有更多文学性意义的话,我想正是在这里。一种充满颓圮感、挽歌式的吟咏,成为正在全面消失的乡村世界真实录影。”评论家张清华说。
每次从城市返回乡村,似乎也没什么事。“回到老家的话——现在回家的机会太少了,回去了也只能待个三五天而已,就是在家里陪爸爸妈妈吃顿饭,看看七大姑八大姨,听他们聊聊村里的事情,回答他们天马行空的问题。”但尽管如此,每一次回老家,都有很多记忆被激活,都有许多新的事物进入他的思维。“只有回去,我才能看到真正具体而平凡的人,才了解人活着的本来面目该是怎样的。”刘汀说。
“当我谈论故乡的时候,我是在说老家”
记者:读《老家》到最后,“当我谈论故乡的时候,我是在说老家”这句话一瞬间吸引了我。在这里,故乡与老家这两个看似相同的语词,忽然生出一些互相缠绕忽远忽近的意味,让读者忽然多出了想象空间。在你的定义里,何为“故乡”,何为“老家”?
刘汀:我特意以“当我谈论故乡的时候,我是在说老家”这句话作为跋,就是为了把“老家”这个概念从“故乡”的概念中抽离出来。
我们都知道,故乡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在古典社会是没有所谓故乡,那时候有的是家、家乡等等。特别是自从现代的乡土小说以来,故乡进入中国文化生活中,而乡愁也逐渐演变成中国知识分子最基本的情感要素之一。这和我们的文化特质有关,和我们作为一个几千年的乡土社会的现代转型有关。只是到了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特别是“乡愁”这个概念的内涵被无限放大以至于无法确切定义之后,故乡的概念又逐渐被“质疑”。当然,从我个人来说,不可能完全脱离故乡或乡愁的语境来进行书写,但我从一开始就希望自己的写作姿态是明确的,我不想做一个传统的怀乡者,不管是美化还是丑化,或者以一个离开者的身份去审视和批判,在我看来都有一定问题。我希望自己是内在于它但又不局限与它的,我肯定要引进知识的、现代的眼光,但我的根底却永远扎根在老家的土地上,根植于老家人本身的伦理和观念中,所以我要提出“老家”这个词。借用索绪尔语言学的两个概念,故乡已成为一个巨大而空洞的能指,而老家则是那个具体而微的所指,我写的就是此时、此地、此事,我不希望自我泛化。
现在想起来的话,我可以说,老家塑造了我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精神维度和心理世界,应该所有人都一样,童年生活有时候决定着我们一生的道路。老家是不可选择的,所以它赋予我什么,我就只能接受什么。但作为一个写作者,可能比其他人要更敏感也更清晰一些。老家是一个乌托邦,也是一个恶托邦,是我个人思想中很多想法的源头,随着年岁的渐长,老家很多看似落后、传统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开始在我身上复活,并且帮助我面对、判断城市里貌似复杂的事物。就像我常说的一句话,一件复杂的事情,如果你把它置换为最基本的逻辑,能说得通,那就是说得通,说不通,那一定可疑。这种基本的逻辑,常常就是老家人的逻辑,农民的逻辑,也是日常的逻辑。
记者:近几年,返乡写作已然成为一种潮流。某种程度上,那是一种知识分子式写作,看到乡村的陷落,试图进行呼吁和拯救。而在《老家》中,我似乎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比如你对乡村伦理秩序的认同和尊重。比如本书中最受好评的《舅爷》一章中,你这样写,“在农村,一切都有它的规矩,人们只是无意识地按着那传了许多年的潜在规矩活着”。“出生时由衷地欢喜,死亡时真切地悲痛,但在生与死之间漫长或短暂的路上,他们总是一种惯性的漠然,但并非冷酷消极。种田收割,吃饭睡觉,婚丧嫁娶,这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最有效的循环。”在我的理解中,这种对乡村秩序的认同,构成了《老家》的基调,也是这本书最与众不同之处。这样的不同,与写作者看待乡村的心态和眼光有关。
刘汀:谢谢你看到了这一点,你看得很准确。这本书最早的责编,在报选题的时候曾经阐述了一段话,后来她专门把这段话发给我,说刘老师,我觉得你这本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跟现在很多流行的故乡书写不一样,你没有刻意去表达乡愁。
我个人不反对任何形式的乡村书写,事实上我自己也不可能彻底摆脱知识分子写作,因为你的思维方式在那儿呢。如果说我这本书里有什么值得我自豪的话,那就是我尽量避免以一种进步的、高高在上的姿态去审视老家和老家人,注意,我说的是姿态,而不是进步本身。这是一种复杂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贯穿始终,我能感受到这些年老家人生活质量在变好,但我也看到了某些东西在崩坏,重要的是,这种崩坏并不是老家人的原罪,他们是无辜的,但却要承受这种崩坏带来的不可控的后果。这是我的悲哀。我要描述并且表达这种悲哀,我想让人们知道在中国北方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人们是如何生生死死的,我想让始终凌虚高蹈的城里人或知识分子看看,农民、乡村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而不是他们口头和文章里的概念、数字、统计。他们也是有灵魂的人。
近些年的返乡写作潮流,我个人是很感到高兴的,我不反对任何方式的乡土写作,有人关注,有人写,就证明许多问题被注意到了,被表达了。但写作者在写作之时和写作之后必须是清醒的,知道自己的立场在哪里、缺陷在哪里,而不是把单一的局部的当成是乡村的整体。对,我反对那种试图以某种乡村写作模式作为唯一的方式的写作,中国乡村表达的整体性必须建立在丰富、独立的差异写作上,和中国的乡村景观本身一样。
“这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必须承受,就像我们的父辈和子孙必须承受他们的命运一样”
记者:在这本书里,《父亲》《舅爷》《四叔》《三叔》这些描写父辈的文章最受好评。你的叙述角度和口吻,其实牵涉到我们这一代人看待父辈的复杂心理。“80后”的成长,正是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最快的那几年。而乡村对于城市来说,是停滞和落后的。从乡村进入城市,父辈的经验以及无法给予年轻人以指导,这种人生道路上引路人和榜样的缺失,是否曾造成你的困扰?你如何理解和看待你的父辈?
刘汀:这本书里写了很多父辈,如今他们已经垂垂老矣,一生基本定型了,该怎么形容他们呢?如果只说一句话,我会说:他们都遵从了自己的命运。他们都活在自己的生活里,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年轻时是否有过梦想或冲动,但最终都回到了自己的命运中来。
从乡村到城市,确实缺少父辈的经验和指导,但我并不以为这些是重要的,相对于外部的指导,我更看重人的内部自我进化。因为缺少领路人而直接面对困境,常常就是进步或蜕变的必要环节,或者换一个说法,在人类诞生和发展的历史上,任何一次自然灾害都可能是推动人类进化的契机,对我也是如此,正是因为父辈经验的缺失,才能让我更加直接地面对城市,我也才能第一时间获得独属于我自己的而不是二手的城市经验。还在读高中时,我就曾经跟同学吹嘘,我说不要羡慕城里人,他们现在过的生活我们将来一定会过上,而我们现在过的生活他们永远也过不上。当然,这也是自欺欺人的想法,但某种程度确实如此。
身处城乡之间,我个人倒并没有太过强烈的自我身份上的夹缝感,但是我有一种难过和悲哀。悲哀这个词矫情了,但的确如此,尤其我看到城里人的挥霍和浪费,而乡下人的局促和窘迫,这种感觉太难受了。每当农产品一涨价,城里人就受不了,他们掌握着话语权,以各种方式呼吁降价,但有谁在乎过种田的人呢?他们没有任何话语权。农作物越来越便宜,但是生活用品越来越贵,这种剪刀差把他们收入的一大部分齐刷刷减掉了。这个我有亲身经历的,比如说羊肉,你在北京和上海的超市里买,好一点四十几块钱一斤,肯定觉得很贵。在我老家,一只羊多少钱?便宜的时候300块钱,一只。我为此感到悲哀。现在大部分刊物的稿酬都能达到300块一千字了,想想一千个字就是一只羊,等同于骨头、血肉、皮毛,以及牧羊人无数的汗水和劳作,这是何等残酷的一个等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也为自己感到羞耻和不安。
记者:在一篇文章中,你这样写道:“我特别想写那些普通人在最庸常的生活里遭遇的不普通的故事。”你的写作偏好是什么?你对自己的写作有何规划?
刘汀:我写小说,也写散文和诗歌,偶尔还写一点评论文字,看起来过于驳杂了,但在我自己心里区分得很清楚,每一种体裁在承担怎样的功能。就像农民种田,要种谷子麦子,也要种玉米豆子,还可能种水稻。当然,这其中我最看重的是小说,它是我的本业,因为小说具有可阐释性,能放进我真正深入思考的东西,而散文是不具备这种功能的。散文不过是我的一种直接表达,包括《老家》在内的散文,写起来对我而言不存在任何困难,似乎是直接流淌出来的,但这里有我最真诚的态度和情感。我的短篇小说集《中国奇谭》很快也要出版了。我相信这部小说集出来,读者会看到一个更纯粹的小说作者的形象。
事实上,我从没有想过走一种更畅销的写作,我对自己的写作本质有认知,我写不出那种极其畅销的作品。退一步说,我也不想写那样的小说,我对自己想写怎么样的小说非常清楚。因为现在的编辑工作,我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稿子,反而对自己的方向更为笃定了。
如果说有写作偏好的话,我愿意概括为:我喜欢用虚构的形式穿透现实,以抵达人的内部精神世界。这听起来像一句废话。具体的规划是,今年可能把想好的几个中短篇写出来,明年开始新的长篇写作,这期间要穿插一些随笔散文或诗。
记者:近几年来,更多逐渐成熟的“80后”作者浮出水面,他们的作品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面貌,这个词语也渐渐脱离以往读者对这一年龄群体的固有认识。“80后”写作,不是只有商业炒作、个人情感、小心情与小确幸等等,而是与前几代的写作者一样,有着丰富的面向和视野。作为“80后”的一员,你会如何看待同龄人的写作?
刘汀:同龄人的写作,这几年的确关注了一些,特别是跟我年纪上下的“80后”作者,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一批写作者正在形成一种稳定、有效的写作方式,写出了一批结构、意识、手法和语言表现都不输于前辈作家的作品,但我们缺少整体上的和根本上的跨越,也缺少真正具有标志性的作品。或者说,这一批作者的作品各占胜场,却没有哪一部作品在历史维度、现实层面、文学本体、哲学思考等综合考量中全部达标,但我相信将来会有这样的作品出现。
记者:青年评论家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一书中,曾提到在面对经济大潮时这一代人的无能为力,身处北京的你是否会感受到外界对内心世界的冲击,面对庞大现实的无力和怀疑?
刘汀:《80后,怎么办?》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他提出了问题,也剖析了问题,他所表达的很多困境我感同身受,但我个人并没有过度的悲观和无力。或者说,我本身就是一个本质上的悲观主义者,对现实世界并未抱有过于乐观的期待,也就不存在失望和失败感。我并不认为我们是悲惨的一代人,因为我经受过更为困难的生活,我以身边的“80后”一代人来看,他们正在获得个人生活,尽管他们失去了统一的历史结构,但今日的现实放在久远的将来去看,同样是历史的,并且同样具有结构性的功能。只是我们身在局中,并不清楚。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并不能再在社会学或心理学的意义上,而只能在年代学上被叫做一代人了。这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必须承受,就像我们的父辈和子孙必须承受他们的命运一样。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