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信息时代如何阅读经典?
韩少功:要有现场还原、心智对接的本事

韩少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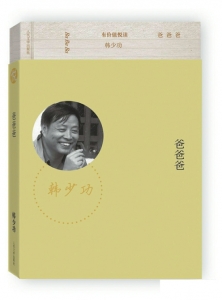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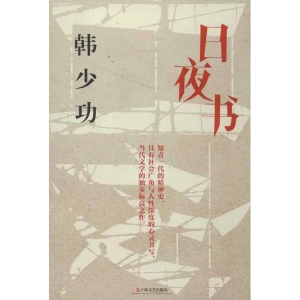
人物档案
韩少功,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等,中篇小说《爸爸爸》《女女女》《鞋癖》等,散文《世界》《完美的假定》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另有长篇笔记小说《暗示》,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散文集《山南水北》等。《山南水北》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暗示》获华文媒体文学大奖小说奖。作品有英、法、荷、意、韩、西等多种外文译本在境外出版。2002年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
书籍如此之多,到底什么是好书?
什么是经典?怎么才能有效阅读经典?近日,作家韩少功对外做了一场公开演讲,专门深入细致地上了一堂关于经典文学的课。
作为一个在文体探索上具有非凡成绩,深具知识分子精神的思考型先锋作家,韩少功的阅读之道,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如何辨别经典?
“共鸣广”不是指“卖得多”
判断是否经典,依然有基本的规律可循。韩少功提到三个价值尺度:创造的难度、价值的高度、共鸣的广度。韩少功在举例“创造的难度”时提到了《尤利西斯》,“比如说《尤利西斯》对很多的读者来说,都很难读懂。我也只读了十分之一就放弃了。但是大家公认它是经典。如果有什么道理的话,恐怕就在于它的意识流手法,深入到人类的潜意识,揭破了幽暗、迷乱、但非常真实的另一个精神空间。同时代的伍尔芙、福克纳也尝试过,但乔伊斯做得更彻底、更高难、更丰富多彩,因此成了一座里程碑,绕不过去的一个大块头。”
“价值的高度”,韩少功则以汉代搞笑大师东方朔和美国笑星卓别林的对比为例,“这两者都是各自所处时代的‘笑星’,但卓别林创作题材的广度和深度是东方朔无法比拟的,东方朔在当时只是一个在今日可称之为“段子手”的存在,而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对工业化的思考,表达出他对世界的批判性思考。卓别林将调侃、娱乐、搞笑变得更有层次和深度,因而后者更有价值含量。”韩少功还认为谢灵运与陶渊明的作品就有价值的高下之分。“谢是著名的山水诗人,他那些诗虽然华丽,虽然优雅,但好像都是旅游诗,是在度假村里写出来的,多少有些花式小资的气味。陶渊明就厚重和宽广得多。他的诗里有劳动,有民众,有情怀与气节。”
作品需要被阅读,就有引发共鸣的问题。在讲“共鸣的广度”方面,韩少功特别强调,共鸣广,“不是指卖得多、读者多,而是指,作品所拥有的穿透阶级、民族、宗教,跨越时间、空间的力量。具有某种普适性与恒久性。比如塞万提斯笔下的《唐·诘诃德》也是一个老“梗”。我们现在看到那些一厢情愿、不自量力、入戏太深的家伙,那些自恋和自大的家伙,通常还会说‘这就是个唐·诘诃德’,可见这一形象已深入人心。”
如何阅读经典?
要有这些本事:现场还原、心智对接
经典作品难读,晦涩,让人很容易敬而生畏。韩少功分享他的几点经验:要具备几项本事。首先就是“现场还原”的本事。“经典大多是前人的作品,总是呈现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与当下读者有经验隔膜。要克服这种隔膜,需要我们发挥一点想象力,设身处地,知人论世,在阅读时尽可能还原当时的现场,减少进入作品的障碍。”
“眼下活在都市的人,习惯于使用煤气和电磁炉,从没烧过秸秆和柴禾,对‘人烟’这个词可能不会有多少感觉。他们从未经历过乡村生活和农业文明,一看到冒‘烟”’那还不打电话119报警?当代人习惯于手机视频通话,大概也不容易对长相思、长相忆、长相恋这一类苦情找到感觉,不容易对渡口、远帆、归雁、家书这一类意象怦然心动。很多人奇怪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为什么那样喜欢写静物,写个街道或修道院,一写就好几页?太啰嗦了。但要知道,那时候他们没有电视,汉代人更没有照相机,作家是让人们了解异域世界的主要责任人。他们不那样“啰嗦”,不那样详细报告,读者可能还不答应,还不满足。他们那样写的合理性,只有放到当时的现场里,才能被我们同情地理解。”
韩少功还提到“心智对接”的能力。财富、科技可积累,直线进步,但在道德、智慧等方面却未必一定如此。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聚焦于女性地位:一个不愿成为男人“玩偶”的新女性,如何打破自己的婚姻困境。鲁迅后来写过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继续讨论这一话题。现在时间过去了一两百年,那个时代早已翻篇,但易卜生、鲁迅所说的问题解决了吗?看看时下的电视剧,有多少个新款“娜拉”还有那里哭哭泣泣,叫叫喊喊?韩少功说,“不难看出,不管生活在什么时代,不论财富和科技积累到什么程度,人的生老病死、恩怨情仇、穷达沉浮,都面临一些长久甚至永恒的难题。前人和我们差不多是同一张试卷面前的考生。那么,如果读经典是有意义的话,无非是这些作品提供了前人的经验和智慧,能给我们帮助。如果我们面对人生考题不得其解,能与前辈同学切磋一番,或向他们打一个‘求助电话’,何乐而不为?在这个意义上,读经典就是读自己,读自己的难事和大事,这样才可能读出一种饥渴感和兴奋感。”
了解对作品造成客观影响的一些因素,很有必要。韩少功认为可以分为“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两方面。像时代、金钱、精英话语权,等等,都是可以影响作品的,他们就是“看得见的手”,比如李安的《卧虎藏龙》在拍完之后,需要用雄厚的经济资本去推广,去宣传,让这部作品的影响力尽量扩大化。效果很好。不过,除了这些“看得见的手”,一部作品的价值高低,最重要的还是看时间,而时间就是“看不见的手”,“时间是公平的,时间会将很多非文学的因素过滤掉,会让人心和作品回归到正常的地位。”韩少功提出自己一个时间长度,“一本书如果过了30年后,还让我们有重读的兴趣,那么这本书则将有可能成为经典。我非常认同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对经典的定义:经典不是你正在读的书,而是你重读的书。”
对话韩少功:
“先锋变成了血液,在悄悄流动”
2017年4月,韩少功成为继贾平凹、余华、格非、苏童、迟子建、西川、欧阳江河等人之后的,北京师范大学第十位驻校作家。身为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主任的作家莫言,赠送打油诗:“楚人肚量大,湖南好汉多。古有屈大夫,今有韩大爹。敢做弄潮儿,不唱流行歌。文学根何在,龙舟下汨罗。”在与韩少功同辈或者较小的国内知名作家中,多位已获得茅盾文学奖,比如格非、毕飞宇。有人猜测,韩少功是最有可能新一届茅奖的人选。
韩少功的生活也引发瞩目。2000年,韩少功选择了曾经插队的湖南汨罗八溪峒,兴致盎然地搭起瓜棚果架,汗流浃背地开荒种地,养鸡喂鸭。他每年大概有一半时间居住在乡下。至今已快20年。有人给他一顶“隐士”的帽子。他本人倒不以为然。韩少功也不鼓励别人学他,尤其是年轻人,“年轻人还是更应该去外面见识到更大的世界以后,再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喜欢乡下的生活。”
当代书评:在传统写作之外,网络文学、类型文学是否也存在经典化的过程?
韩少功:很多网络小说,写得太长了。动辄几百万字。实在让人没有足够精力去读完。但是我认为,文学不能因为介质不同论高下,纸媒发表的作品都是好的吗?泡沫和垃圾也很多。真正好的作品,在发表出来的作品,一般也就占到百分之十的样子。
当代书评:你本人在创作早期,对文学的文体、语言有很强的先锋探索。但现在你的作品有向主流叙事方式靠拢的趋势。为什么呢?
韩少功:人们习惯从作家的变化里找出深刻的含义和深远的预谋,但作家不是按照一个严密规划来写作的。作者的写作往往不是按照严密的规划的。有些变化就是一时的情绪,一个偶然的机缘所致,没有深远的预谋。而且作家在创作上往往喜新厌旧,不喜欢做重复的事,变化是不讲道理的。
当代书评:文学的先锋精神还存在吗?
韩少功:每一种实验,提供给人类的营养会长期存在。不能说现代主义消失了,现代主义就死亡了。现代主义消失了,也许现代主义就永生了,它融化到其他各种文学的创作手法和技巧里。三十年前的先锋作家们,当他们通过早期的先锋实验以后,已经改变了自己,先锋变成了血液,在悄悄流动。文化的事情只有加法没有减法,不会有完全消失掉的东西。
当代书评:你如何看待今天的知识分子自主选择回归乡村的生活方式?
韩少功:我选择乡下,是跟我个人的性格有关,我不好热闹,喜欢安静,每当从人多的地方出来,就感觉自己变傻了很多。只有回到乡下,我才恢复我自己。但我称不上“隐者”,因为一个电话
都能把我找到。我也不算真正的农民。首先我不是全部时间在那里,第二我还拿着工资,和农民的生计来源不一样。种地是我的园艺爱好。有年轻人想要模仿我,也到下乡。我赶紧阻止:别别,你要先去外部世界打拼,多看看世界,把这个世界弄明白以后再说。看了世界之后,再来决定你愿不愿意选择乡下生活。对写作者,浮躁是文学的大敌,任何时候都要气定神闲,有自我的定力。但这并非只有乡下才能拥有定力。
当代书评:文学的价值意义在哪里?
韩少功:如果是指现实利益方面,文学的作用很小。除了极少数的情况,文学很难让人赚大钱。很大一部分人,不能因为文学收入而谋生。但文学可以让人的生活得有意思,感受到意义。不管贫富成败,哪怕是一个罪犯、恶棍,生命总也会有需要文学的时刻。只要他还有想象和回忆,需要温暖和精神支撑,这个时候,文学就到场了。有人说,文学对社会人心进步的用处在哪?这个世界依然有犯罪现象。我想说的是,同样的问题也可以问其他学科。文学不能独自承担社会落后或前进的责任。文学不可能把我们带入天堂的境界,但是它能阻止世界变得更坏。
当代书评:有人预测,你可能是茅盾文学奖的下一个获得者。你怎么看待文学奖的存在?
韩少功:评奖是促进文学的一个工作机制,但是文学毕竟不同于体育竞技。很多文学奖,评奖结果一出来,就引发不少争议。其实,这都正常,本来文学的评判标准就很难统一。我们对文学奖,也不要过于迷信。看看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名单,有多少是值得重新读的真正的经典作家,这也是一个问号。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