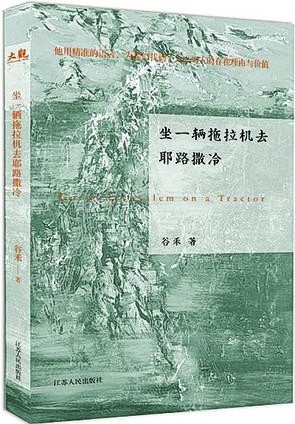
《坐一辆拖拉机去耶路撒冷》 谷禾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
■杨碧薇
恰如《坐一辆拖拉机去耶路撒冷》有意无意的暗示:当“拖拉机”启动时,泥土的清香气息迎面扑来,不忘吞吐一缕旧时光的余韵;而遥远且陌生的“耶路撒冷”,是这趟乡间旅行的目的地,它充当了未来的象征,亦是一种现代的隐喻——只要你静下来聆听谷禾的诗歌,就会听到反复回响的“怀旧(田园)/现时(城市)”的节拍。它们就是谷禾的诗歌大厦最稳固的两块基石。
田园,是诗歌永恒的同俦。一千多年前,陶渊明感叹:“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因着“田园将芜”的危机,他毅然选择了“归”。如果说,陶氏的“田园危机”主要指向精神困惑,那么,一千多年后,谷禾所面临的“田园危机”在精神的向度外,还有着切切实实的现实性。
这一现实性是沉痛的。和所有接受过抒情诗教化的诗人一样,谷禾反复写到田园风景。“三两颗星,一片闲云,半枚月亮”(《一辆锁紧的单车》),“村庄,鸟巢,乌鸦的叫声”(《雪在烧》),还有流星、溪水、蝴蝶、蓝天,都是他诗歌筵席上尊贵的客人。纵然,他笔下的田园已是旧日幻影,再美好也与今日生活毫无真实的交叉。成片涌现的它们,不过是忙碌的都市人在午休时分的白日梦,梦醒后,一切又成碎片,粘附在城市浑浊的空气里。显然,谷禾并非为了田园而写田园,他很清楚田园在现代生活中的虚幻性,所以,当他细心地描绘白鹿吃草的纯美画面时,不忘通过题目提示读者,这般佳景仅仅是一阵冥想(《对一头白鹿的想象》);谈起故乡“井壁上的青苔,井底沸腾的星辰”时,也未回避如今“河流干涸了”“亲爱的母亲你老了”(《回忆一个村庄》);他在城郊散步时,更是悲哀地看到“树杈间的鸦巢、坟墓、星星、虫鸣、待拆的农舍/都消失殆尽了”(《散步诗》)。
田园荒芜,那么城市呢?谷禾写城市的诗歌并不少。《朝南的窗子》写小区家庭生活,《老王咖啡馆》写剧作家开咖啡馆的故事。地铁,则是谷禾诗里最真实的城市景观。“从地铁口吐出来的人们,低着头,行色匆忙/一边在朋友圈里刷着存在感”(《下班途中,过地铁北运河西站》),可谓一幅时代速写;“地铁站在北运河的黑暗中闪着灵光”,既是眼前实景,也是诗人心象的映射。尽管每天与地铁打交道,谷禾并未因此丧失诗人的直觉:于他而言,地铁这个工业革命的产物,始终有抹除不了的陌生性。从陌生性出发,他进一步思考物与人的关系:“一座城市的两端/像生命的两极,而连接它们的地铁/又隐喻什么?”(《给女儿,或一次争吵后》)。
虽有为数不少城市题材的诗歌,但对谷禾这一代诗人而言,写乡村(田园)还是城市(现代文明),是一个隐秘且艰难的抉择。他们中的不少人有着从乡村移居城市的经历。当现实生活不如意或无法达到预期值时,乡村就化身为乌托邦,成为精神上最后的阵地。因此,他们乐于写乡村,尽管那个记忆中的乡村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早已支离破碎、不复存在。从某种程度说,对乡村的泛滥书写,已成为新诗里一种低成本的复制,其核心是媚俗的虚假,很难为新诗提供有创新性的养分。从这种写作潮流中抽身,需要独立的判断和抵抗的勇气。谷禾的优势是,他并未沉浸在乡村/田园的虚假美梦中,而是毫不遮掩地写城市,既写城市的乐趣,也写城市的空虚。他早已清醒地意识到,就像《边城》里倒塌的白塔所预示的,田园已芜,自己没有回头路;真正的诗人,要勇于面对碎片化、失焦的现实,通过诗歌建立一种新的秩序。
谷禾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要建立新的秩序,真正的力量在高处,它来自于对宇宙奥秘、生死悲欢的探询。这样的诗歌在谷禾诗里几占半壁江山。首先,在世俗化的祛魅生活里,他依然葆有对死的凝视。在《百年孤独》里,阿玛兰塔看见的死神是穿蓝衣服的妇女,谷禾诗里的死神则“戴一顶五颜六色的帽子”,“死神远远地望着我/有时也走近了/摸一摸我的手/……把我抱在怀里一小会儿/一句话都不说/像抱着自己亲爱的孩子”(《死神戴一顶五颜六色的帽子》)。因为对死的迷思,他又专门写灵魂,希望灵魂即使是“烟雾一样飘散在宇宙深处”,也要“寻找新的生命体再次诞生”(《灵魂说》)。其次,他的诗总能与生命产生直接联系。看云时,他感受到生命的孤独与荒凉(《十万云朵》);看树叶时,他联想到命运的轮回(《身边的树叶》)。从对死的恐惧里,繁衍出对生的珍惜,这不正是对生命本身的敬畏吗?最后,谷禾的诗歌始终保持向上仰望的姿势。他仰望星空,看到星空“浩瀚。鼎沸而寂静/风吹微澜/仿佛世界还不曾开始”(《星空记》),他渴望流星“把我带去那浩渺的,深邃的,神秘的宇宙深处”(《目击一颗流星》)。如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耶路撒冷”理解为高处的力量,唯有它能拥抱寰宇、洞察生死,并穿透在俗世纷扰中日渐坚硬冷漠的人心。
谷禾自称悲观主义者,但在悲观的冰层下却埋藏着似火热情。诗集第一首诗《雪在烧》不正表现了冰火交织的盛景吗?这埋藏的热情源自生命本能,催促谷禾迫不及待地歌唱春天:“当春天来了,你指给我阳光”(《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在春天,/喜悦远不止于此”(《你好,春天》),“它有香椿的滋味,春天的滋味”(《香椿记》),“你看呵,美好的春天来了,万物生猛”(《春节戏作》)……对生命的热爱与执着,保护着诗人远离悲观主义的魔障。米沃什曾说:“人用废墟中找到的残余来建造诗歌。”现在,即便田园已芜,谷禾仍背着手站在破碎的后现代废墟上,仰着头,坚持向上的守望。
诗人的守望,正好佐证了汉语新诗存在的必要。在传统的田园价值体系崩解之后,在现代性举步维艰地寻找有说服力的意义之时,汉语新诗一直在进行现代中国精神的建构,它就是一种守望,它就是提前到来的未来。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