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渔村小雪图 宋·王诜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云居寺山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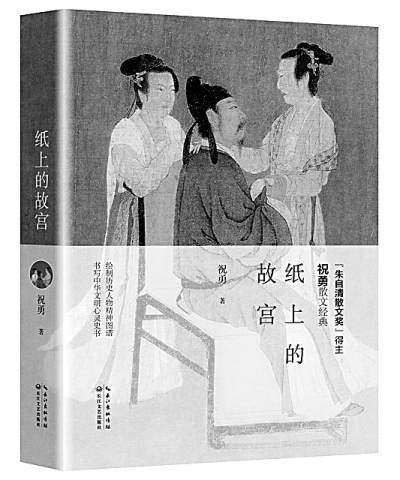
《纸上的故宫》 祝勇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枯木怪石图宋·苏东坡
毫无疑问,我们当下正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快速、越来越便捷的时代。但是,只要是曾经领略过古老中国文化那宁静辉光并于其中提取到精神滋养的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这也是一个越来越粗砺、越来越容易走神的时代,因为文化之“美”从来都与“高速”绝缘或悖反。祝勇就属于怀此慨叹之人。在《纸上的故宫》中,他说自己有一种“偏见”,即认为“只有在农耕文明中,人们才会对艺术产生膜拜的感情,随着农耕文明的瓦解,唯一可能成为艺术的就是为艺术准备的挽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农耕文明”曾经全面而深刻地将人与天地万物联结在了一起。在那样的生活里,人们不慌不忙,起居有度,身、心、灵按捺不住地散发着自然的芬芳,对艺术的崇尚也能够保持纯粹高放的品质。
因此,祝勇选择的书写对象,无不具备“农耕文明”那缓慢、安静、朴素的质地。简淡清净的云居寺,皎洁安详的阿坝,平滑如镜的上林湖,哺育万民的围屋和楠溪江,从岁月深处生长出来的婺源古物,京都木屋里寡淡洁白的清水豆腐……这些凝结着大拙、大美的事物仿佛与生命的流逝无涉,甚或可以说,它们将时间之箭扭转了方向,朝着天地玄黄的来处将自己镀上了层层古老的光晕。只有像祝勇这样对美具有高度敏感和信任,并能够持之以恒进行追索和琢磨的人,才能拨开混沌的枝蔓,将它们的本真面目辨认出来。比如,在一个黑如墨漆的深夜,当他在德格印经院里用手触摸经书雕版上凸起的字迹轮廓时,他完全“看到”了它们的形状,读懂了它们保存着的智慧,从而安心虔敬地接受那暗夜里庄严圣洁的照耀。
沿着这一逻辑,我们可以断定,能够在如是纯朴、不掺杂质的物事中看到“美”、礼赞“美”的祝勇,必定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完整的美学认知谱系。这套谱系拒绝现世的凡俗利益,剔除了工业时代的急躁粗糙,绝不妥协于人云亦云。甚至,它还具有自我过滤和生长的功能,能够将精神之美搭筑为高塔,使所见与所得互现互证,互为良性循环。
如果说物象之美是静态的话,那么,更让祝勇击节赞赏的是充满生命力和文化深度的动态之美,如王羲之、李白、苏东坡那样狂卷着历史波澜、镶嵌着审美维度的人生。写这三人,祝勇均从自己熟知且极为钟情的书画作品入手——王羲之的《兰亭序》、李白的《上阳台帖》、苏东坡的怪石墨竹。他把历史知识、文化博闻、艺术领悟的经纬融入笔端,通过研究撇捺的流转、墨迹的浓淡、留白的气象,不仅读出了他们人格的洁净和高远,而且铺展出了与之相关的美学史、文化史、艺术史。关于王羲之,作者通过史实的还原,以富有动感和画面感的文字描摹了永和九年的那场盛世之醉,描述了王羲之在书法中寄寓的精神之苦,向我们展示出一个残缺但不乏慰藉的结果:《兰亭序》的真本下落不明,但后世文人却通过对它的临摹建立起了一个绵延不绝的美学共同体。换言之,王羲之“缺席”的墨宝以另外一种形式始终“在场”,并开启了中国文人精神王国的建构之旅。
至于李白和苏轼,祝勇着墨更多的是他们的浪漫有趣、乐观旷达、高蹈的性格、深邃的孤独。看得出来,他格外喜爱并迷恋这样的人格。而有意思的是,这两位中国历史上千古难逢的奇人恰恰都是以对儒家文化的反叛、僭越而自我成长为了独立的美学个体、文化的有机体。祝勇写李白、苏轼,并不拘囿于其文、其才,而是以历史主义的广阔视角将他们精神世界的成型与时代背景联系起来:唐朝以对驳杂的游牧民族文化的包容含纳而孕育出了成色纷杂、酣畅任性的“大唐李白”,他住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是我们的遗传基因、血液细胞和精神密码;宋朝则以文化的雅趣广博、文人的知己情怀安放了“仅次于上帝的人”苏轼,他“以出世的精神入世”,创造了新的人生观,也给中国人留下了新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资源。在作者看来,这与其说是他们的幸运,莫若说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幸运。因为他们都是“大于时代的人”,他们给予时代的,远远超过时代给予他们的。中国文化和精神的深度也因为他们而大幅度地得以提升。
祝勇以清朗俊逸、饱含诗性和暖意的笔墨追溯和描摹着历史深处的文化之美、精神之美,但作为一个现代人,他要做的绝非“复古”,而是要以现代人的观察和智慧在“旧”里读出“新”,在古老帝国的追忆里完成个体生命的哲学思考。《纸上的故宫》写中国文人如诗如酒的快意人生,写汉武帝雄心万丈建功立业,写李自成功败垂成孤独亡命,写“定远”舰沉默如谜的残骸,写京都寺庙里的枯山水,还有清兵之墓,马关之殇,中山之约,实则都指向对人生终极命题——“时间”的思考。
祝勇将中国文人对生命的朴素忧思与其创作联系,将中国循环的时间观与西方的线性时间观相对比,将历史的风起云涌与人之生命本质相联系,收获了丰富、辩证而多面的思考与书写,这种书写具有极强的延展性与纵深度。在他纵横捭阖的对比与联系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和精神以纵贯千年的柔韧讲述着亘古弥新的真理:从时间哲学来看,“中国人在循环中找到了对抗死亡的力量,因为所有流逝的生命和记忆都在循环中得以再生”;从精神美学来看,“中国传统的审美记忆”以力量和担当“收束于优雅艺术与人格中”。我想,对于祝勇而言,中国人的时间观与美学观是彼此互涉、一体两面的,它们同样具有柔软坚韧和品格和流动轮回的形态。而这种“超越物理力量”的精神之美、之力,是中国之为文明之国的精髓所在。
这是一种饱满蓬勃、强劲回流的文化的自信,精神的自信。无论我们的时代前进到何种程度,这种内在的支撑都是无法被取代和抹除的。我以为,《纸上的故宫》正是在文化关注度日益稀薄的当下,重新为我们注入了美的力量。它所展现出来的智性诗意与辽阔气度,使读者的心性能够得以重新沐浴中国文化的温煦之光,并抵达精神之美、生命之思的充盈与浩瀚。
(作者:曹霞,系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