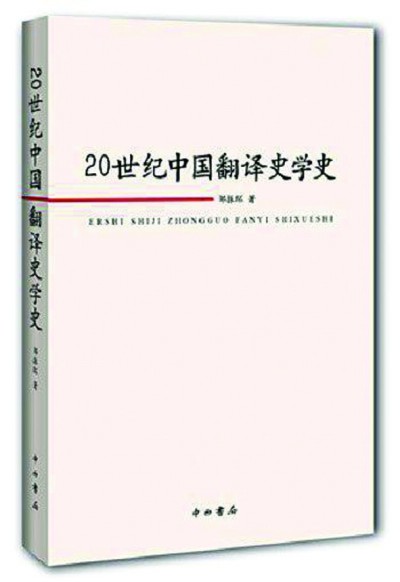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 邹振环 著 中西书局 出版
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史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历了100多年的演进过程,晚近30余年,翻译史研究的势头更是有增无减。如此一来,为了回应翻译史研究发展的需要,对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历史进程进行清理与回顾就显得尤为必要。邹振环的新著《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以下简称《史学史》) ,就是对中国翻译史研究在20世纪的形成与演进的历史性回顾与反思。作者把中国翻译史学的研究内容分为“中国翻译史学原理”和“中国翻译史学史”两大部分,如书名所示,他所关注的是后者。具体而言,《史学史》是“对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成果作出一次比较系统的再总结和回顾,提示一条20世纪形成和发展的翻译史研究的谱系”。
综观整个译学界的研究现状,翻译史学史似乎并未引起学人的兴趣和关注。以翻译史实践为对象的系统性专题研究,严格说来,在《史学史》面世之前是空缺的。显然,《史学史》所做的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也是对20世纪学术史的有益补充,“填补了20世纪史学学科研究史上的一大空白”。《史学史》立足于“描述、批评与反思”的研究路径,为勾勒与重现、分析与评判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本体面貌与脉络演变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有效的实验。
作为学术研究史,《史学史》的首要任务是要对20世纪翻译史研究的历史进程加以概括,并对其作出系统的描述和梳理,这就必须构建内部结构,也即各个构成部分的组合关系。针对这一问题,需要考虑两层关系,即横向的空间轴系和纵向的时间轴系。作者在横向上选取内地、香港和台湾三地的翻译史研究为考察对象,在纵向上则以1902年为起点,将1902-2000年分为1902-1949、1949-1984、1984-2000三个时期;同时它又以时间为经,以具体的研究个案的主题为纬,一纵一横,一经一纬,构建起了《史学史》的叙述结构。
《史学史》立足于历史文献学的方法,采用知识史理论,以“起承转合”为演变轨迹,对百年中国翻译史研究作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纵横描述。在具体的描述方法上,它以治史者、史著、刊物、编纂形态、翻译史研究现象等“散点”来把握20世纪翻译史研究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特点。以“点”带面,在对“点”进行重点描述时,不忽视历史内部的照应与关联以及整体性流变。在横向的空间轴系中,《史学史》将内地、台湾和香港的翻译史研究并置于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的整体架构中,展现了“中国概念的完整性”,由此形构了一部“全景式”的翻译史学史。
历史研究除对历史事实进行综合性的整理与描述之外,断然不能没有价值评判。毫无疑问,《史学史》的贡献还在于它从史学批评的角度,重新审视了20世纪翻译史研究活动及其成果的学术价值。《史学史》把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史著(包括翻译史研究现象或事件)置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双重空间中,对百年翻译史研究的现状展开了局部性与整体性批评,检讨了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利弊得失。《史学史》坚持“务成曩美,毋薄前修”的批评态度,持客观公允的立场,实事求是、设身处地地作出评价,且做到要言不烦,点到为止。
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史学史》大致有三条批评路径:一是宏观把握20世纪翻译史研究的学术流变,并以此确立翻译史著的历史地位;二是秉承古代学术批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清晰呈现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发展的一般形态,并确立翻译史研究各种趋势和潮流在历史演进中的位置;三是运用历史比较法,阐明20世纪翻译史研究的进程特点和翻译史著的优长短缺。
而在对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展开描述与批评的同时,该书还对其进行了学理反思。这些反思不是凌空虚蹈,而是建立在对20世纪翻译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与现状特点的全面把握与深度理解之上。
首先,《史学史》对20世纪翻译史研究的发展进程与内外动因进行了反思。从研究主体、研究规范、传统治史方法以及学术交流等因素反思了治翻译史的发起和发展,并从物质经济和教育发展的角度检讨了1949年以前翻译史研究系统性的缺失。在对20世纪中期中国内地翻译史研究的承势与转折的考察中,《史学史》就时代政治对翻译史研究趋势的影响作了深入剖析。与此同时,该书就同一时期台港翻译史研究的不同局面的成因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对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的翻译史研究,《史学史》分析了这一时期翻译史研究回归学术自身的自律性。20世纪最后20年是中国翻译史研究的重要时期,《史学史》从史料开掘、研究方法、研究规范等方面思考了“多元格局”的治史局面的形成。
其次,《史学史》对20世纪翻译史研究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了反思。一是研究主题的分布不平衡。《史学史》指出,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已经形成了多学科、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特点,但研究主题偏重佛典翻译史和文学翻译史,从而造成了研究整体格局的失衡。二是史料与史识的结合不到位。《史学史》认为,在有限的翻译理论史和翻译思想史研究著述中,大多长于叙述和对资料的梳理排比,缺少对史料的探究和升华。三是研究方法上缺少创新。《史学史》指出,20世界翻译史研究缺少历史研究新方法的运用,多为 “断线式珍珠”的传统叙述模式。《史学史》也触及到了翻译史研究的理论问题。它认为,20世纪初以来的翻译史研究在理论上并未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话语系统,翻译史尚未建构起属于自己学科的文献学。
再次,《史学史》对于20世纪翻译史研究对新世纪研究的启示也作了深入思考。它从新史料的挖掘、拓展、汇编与辑印,新理论与新方法的运用,以及翻译整体史与专门史的同步发展等角度,思考了21世纪翻译史研究的目标与方向。
 时刻新闻
时刻新闻